

1月10日,在2017年國家發改委的第一場新聞發布會上,徐紹史主任表示,2016年是供給側改革開局之年,“三去一降一補”取得了初步成效——鋼鐵去產能4500萬噸,煤炭去產能2.5億噸,安排的職工接近70萬,商品房待售面積連續10個月下降,市場化債轉股和企業兼並重組也在有序推進,實體經濟的成本有所下降,重點領域的補短板工作也取得了積極成效。
而在這些數字之后,改革大潮中的人們又是如何度過這一年的?人民財經選取了五位普通百姓的2016年,這其中有苦有甜,有思考也有成長,隨著供給側改革的推進,他們也在腳踏實地地接近自己的中國夢。
(策劃:夏曉倫 劉然 楊迪 喬雪峰 孫博洋 孫陽 賈興鵬 王子候 楊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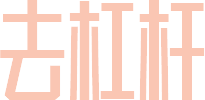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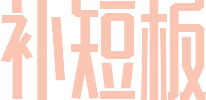
山西晉城南郊,岳南煤礦爛尾的辦公樓在寒風中顯得格外蕭瑟。
曾經熙熙攘攘的礦區,已經變得幾近荒蕪——庭院中雜草叢生、垃圾遍地,澡堂天窗積滿了黑灰,更衣櫃鏽跡斑駁。
44歲的趙燕兵正准備下井。作為岳南煤礦的一名安全員,他的主要工作職責是檢查各項礦井設施的正常運轉,確保工友的下井安全。參加工作20多年的他是個地道的“煤”二代——70多歲的父親也在煤礦上工作了一輩子。可以說,他的家庭也是煤炭產業興衰的見証人。
在煤炭行業興盛的時候,雖然工作辛苦,但干得多掙得也多——像他一樣的一線工人每月收入能達到六七千元。
然而,從2012年開始,全國過剩的煤炭產能致使煤價“跌跌不休”,進入2016年時,煤炭行業的下行態勢已經持續了4年。從2015年2月份起,趙燕兵所在的煤礦就已經全員停發工資了。截止10月份他已經有20個月沒有領到工資。行業的不景氣不僅把山西經濟拖入谷底,更讓他這樣的煤炭工人切實感了生活的壓力。
2015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去產能”確定為2016年五大結構性改革任務之首。在煤炭方面,中央要求從2016年開始,用3至5年的時間退出產能5億噸左右、減量重組5億噸左右。
大力去產能,人員分流勢在必行。在去產能的壓力之下,這個曾經3000多人的“地方大礦”,每天隻剩下十幾個人下井進行簡單的排水作業。趙燕兵沒有被分流,雖然“干半天休一天”,但他仍留了下來。
也許是20多年工作的慣性,也許是勤懇的性格使然,即便工作變得“半死不活”,但隻要有人下井,他作為安全員也時刻不離。在該上班的時候,他仍然堅持早七點從市區的家中出發,驅車趕往30公裡外的礦上准時簽到。
為了養家糊口,趙燕兵開始尋找“兼職”、謀求出路。
“像我們這樣從煤礦下來的人,跑滴滴是目前比較好的出路了”。對於缺乏專業技能,又需要照顧家庭的趙燕兵來說,做滴滴約車司機是一份合適的兼職。每天,差不多也都是“跑到困”才回家。在這個人均收入不足2000元的小城裡,每月1000多元的收入,讓這位礦工非常重視這份兼職工作,而這份“額外工資”讓拮據的家庭有些許緩和。
據悉,目前像他這樣的礦工轉行司機,佔到整個晉城網約車司機一半還要多。
伴隨去產能,山西有序開展化解產能企業職工實名制錄入等工作,明確內部安置、外部分流、轉移就業、創新創業、自主擇業、培訓轉崗、內部退養、靈活就業、公益性崗位托底安置等多種方式。據《山西日報》報道,截止2016年11月底,去產能煤企已分流安置17914人,佔應安置總量的85%。截至2016年10月底,山西已停產關閉25座煤礦。全年退出煤炭產能2325萬噸,居全國第1位。

2015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去產能”確定為2016年五大結構性改革任務之首。2016年年初,鋼鐵、煤炭兩行業去產能路線圖《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脫困發展的意見》與《關於鋼鐵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脫困發展的意見》相繼公布。中央要求從2016年開始,用3至5年的時間退出產能5億噸左右、減量重組5億噸左右。
大力度的去產能工作之下,職工的安置是各級政府最關注的環節。據估算,去產能工作將涉及鋼鐵行業50萬職工和煤炭行業130萬職工的工作崗位。再算上水泥、玻璃、電解鋁、船舶等行業,去產能帶來的再就業壓力著實不小。這不僅是企業面臨的難題,更是整個社會面臨的大事難事。
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日前表示,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已初見成效,去年去產能的年度任務已經提前超額完成。徐紹史介紹,我們確定的鋼鐵去產能目標是4500萬噸,煤炭去產能目標是2.5億噸,這些產能涉及到需要重新安置職工,煤炭2.5億噸的產能涉及到62萬職工,鋼鐵4500萬噸的產能涉及到18萬的職工,到去年年底安排的職工已經接近70萬。
經過一年卓有成效的工作,去產能任務已經提前超額完成。但一些分流職工的生活並不容易。政府的主要職責是“托底”,地方政府將轉移就業、創新創業、培訓轉崗、內部退養等多種安置職工的良策做實做細、配套資金及時到位,才能最大程度降低去產能過程中對困難職工及社會轉型帶來的陣痛。

“市場不好的時候,3天賣不出去一套房,而現在,1天能賣出去3套。”說起唐山的樓市,田野用“過山車”來形容。從小就害怕坐過山車的他,卻選擇了房產銷售這樣一個職業來挑戰自己。
老家在河南,23歲的田野,已經是一名擁有4年房產銷售經驗的“資深人士”。然而,即使是他這樣的資深人士,在2016年10月以前,也拿過好幾個月2500元的底薪。
在北京燕郊、大廠等賣過一段房子后,去年年初,田野跟隨著團隊去了唐山的房地產項目。唐山距離北京較遠,根本吸引不了外來的購房者。
“當時唐山的庫存驚人,僅一個項目便有近5000套住宅待賣,”雖然開發商想了很多促銷手段,甚至降價銷售,卻依然無人問津。
“3天賣不出去一套房!”這對於主要依賴業績的房產銷售來說,簡直就是一個折磨,每個月僅2500元的底薪,連吃住都不夠用,還要借外債。
轉機出現在2016年10月份,北京“9.30新政”出台后,北京周邊如通州、燕郊、大廠等地區的房源急劇缺少,另一方面受京唐高鐵的帶動,以及唐山市政府對重工業企業的轉移,唐山又重回購房者視線。
短短幾日,風雲突變。唐山成為購房者的香餑餑,其中又以投資者居多。
“以前是我們追著客戶賣房子,現在是客戶主動找我們了解樓盤信息。”
從乙方到甲方的瞬間轉換,讓田野居然有點不適應,然而忙碌讓他很快便忘記了這些,每天他沉浸在帶客戶看樣板房,簽購房協議的快感中。“有次兩天賣了7套房,提成便達到六七萬。”
賣方市場,房價自然也跟著漲,唐山的房價也一路從5000多元,漲到了7000多元每平米,而田野所在的樓盤項目,近5000套住宅也在短短兩三個月時間一掃而光。
唐山“神速”的去庫存過程,讓田野這樣的房產銷售直接獲利,業績好了,腰包鼓了,“比去年多掙了三五成吧”。田野坦言今年可以開心回家過年,然而面對“過山車”似的房地產市場,田野最大的願望,是中國樓市的平穩,是所有人都不再為“住”而憂傷。
當然唐山只是一個例子,田野也僅是萬千房產銷售中的一員。它們的背后,實則是中央和地方開足馬力去庫存的大背景。
在降低首付比例、發放購房補貼、稅收優惠等一系列政策的影響下,2016年房地產去庫存效果顯著。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去年11月末,全國商品房待售面積比10月末減少427萬平方米,全國房地產庫存量已經連續減少9個月。
【詳細】

在去年12月份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定調2017年房地產走向,提出了“房子是住的 不是用來炒的”。實際上,去庫存過程中也應避免“炒作”因素。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國房地產庫存,大約七成集中在三四線城市,這些城市的房地產庫存不僅量大,而且去庫存乏力。
三四線城市如何去除庫存,還應回歸“房子是人住的”這條總規律上來。我們看到,不論國內與國外,凡是經濟活躍度高,外來人口輸入多的地方,房地產總是供不應求,房價也相應高漲不下。反之則大量房產積壓,無人問津。
一些地方政府想通過政府補貼,信貸優惠來吸引人們來買房,消化過剩房產庫存,雖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仍然是治標不治本。
要想真正消化過剩的房地產庫存,關鍵還是怎麼把人吸引到城市裡來居住生活。比如,創造更便利的投資創業環境,讓更多的人來此地創業投資,發展產業,提升經濟活躍度﹔比如,放寬戶籍限制,讓更多的農民工能夠享有城市居民的公共福利,創造更多就業機會,讓更多的農民進城生活居住﹔再比如,承接一線大城市疏解的城市功能,承接一線城市轉移的產業。
總而言之,三四線城市去庫存,要從吸引流入人口上做文章。打造一座讓人願意來,來了能住得下的城市,住下就不想走的城市。讓“庫存”變成促進當地經濟發展,人民安居樂業的助力。

“企業進入了‘寒冬’,不代表我們就可以跟著冬眠”,作為一家全國性商業銀行山西分行的客戶經理,談起“去杠杆”中的企業與金融機構,年輕的龍偉始終把“責任”二字挂在嘴邊。
樹不能長到天上,高杠杆催生高風險。長期以來,我國企業以債券和信貸為主的融資結構,直接股權融資等其他融資方式發展相對滯后,從而導致企業的資產負債表急劇膨脹,杠杆率持續攀升,“去杠杆”勢在必行。
“如果說高杠杆是企業的切膚之痛,去杠杆就是刮骨療傷”,山西某省屬國有獨資大型企業的負責人表示,雖然長遠來看“去杠杆”是必經之路,可當下的日子著實不好過。
日子難過怎麼過?企業自身先想辦法。
作為山西這個資源大省的重點國企,這家企業前期主要以煤炭、鋼鐵、有色等大宗商品的運銷為主營業務。然而隨著“去產能”步伐的持續推進,加之全球性鋼鐵、煤炭產能過剩,價格下跌導致企業經營壓力日益增大。
“我們也及時調整了戰略,逐步降低煤炭及鋼鐵等業務比重,加大了有色金屬板塊份額”,這位負責人說。企業的戰略轉型不可避免的迎來了“陣痛期”,由於業務變更,企業銷售收入大幅下降,一些銀行也開始隨之抽貸,這家企業陷入現金流緊張、新業務受阻的惡性循環。
企業難過怎麼辦?金融機構實現助力。
龍偉認為,“去杠杆”也要因地制宜、因企施策。“我們調研中發現,雖然這家企業銷售收入下降明顯,但利潤較去年差距不大,且效率利潤率獲得大幅提高,企業盈利能力增強了”,龍偉表示,基於企業短期內資金壓力大但盈利能力增強、戰略轉型初顯成效的現狀,銀行不應袖手旁觀。
“去杠杆的進程對企業和我們這樣的商業銀行,都是一次淬煉蛻變的機遇”,龍偉所在的銀行在看到了企業生命力,決定加大對企業支持力度,授信品種從短期流動資金貸款轉變為中長期經營補充貸款,以緩解企業短期資金壓力,助力企業順利轉型。
與此同時,龍偉還幫助企業進一步優化拓寬融資渠道新模式,為企業增加了SCP、PPN等直接融資工具在融資結構中的比重,保証流動性充足。
“我們創新產品模式,為這家企業提供了PPN(非公開定向債務融資工具)項目,10億元的注冊總目前已成功發行了2億,企業現金流得以明顯改善”,龍偉說。
去杠杆不是墨守成規,更不是對實體企業“一杆子打死”,作為重要利益相關方,銀行也應對自身進行一次供給側改革。“幫助企業解決融資問題,設計融資方案,解決企業正常經營運轉所需的現金流,這就是我的工作,對工作就應該負責嘛”,冬日的陽光下,龍偉笑著對記者說。

隨著“去杠杆”任務的推進,企業正向著“輕裝上陣”的正確方向邁進。數據顯示:截至去年11月末,我國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為56.1%,同比下降0.5個百分點,“去杠杆”成效初顯。
然而,改革的推進也會有新的難題亟待破解。“去杠杆”的本質是催生實體經濟活力,是“換血”而不是“抽血”。簡單通過收回貸款來降低負債和風險,會讓“寒冬”中的企業雪上加霜,無疑背離了政策本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要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也要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當此關鍵節點,金融部門要做的是突破傳統信貸融資業務模式,著力創新金融產品、拓寬融資渠道和手段,因企施策、積極作為。
最大的決心會產生最高的智慧。在“去杠杆”的過程中,沒有局外人和旁觀者,我們需要的是更多有智慧和勇氣的“責任人”。

來料加工、借船出海,說起東莞制造,許多人固有印象就是兩個字:“代工”這也就成了曾經的“世界工廠”東莞身上,一個最著名的標簽。
16歲離鄉入伍,17歲喪父,24歲回鄉創業……為了追求夢想,何思模扒過火車、撿過破爛、賣過血,什麼苦都吃過。
2001年,這位易事特電源股份有限公司的掌門人靠著3000元銀行借款開始創業,以生產通信電源起步,開了一家小型工廠,主要為一些國際知名品牌代工,貼牌生產電源。
雖然代工利潤微薄,隻有6%,但是何思模憑借著“拼命三郎”的創業干勁,逐漸在東莞謀得一席之地。
2008年開始,伴隨著國際市場變化、人口紅利開始消退等多重因素,東莞制造業無法再利用密集的勞動力創造更多價值。
訂單減少、勞動力成本飆升……這座曾經的制造業重鎮,在經歷了持續的經濟下滑后,一系列弊端開始顯現。
當時,企業需要為一線普工每人每月支付3千至4千元的成本,相當於緬甸、越南等地的兩至三倍,一批產品技術含量低、資源消耗高的企業相繼倒下或離開,昔日的“東莞奇跡”面臨著難以續寫的艱難考驗。
何思模也同樣需要直面這一難題:工廠該怎麼辦?是就此倒掉,還是浴火重生!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隻有直面痛處,下定決心轉型升級,才能贏得未來。何思模抓住時機,以很優惠的價格收購了施耐德所持的部分股權,進軍光伏新能源領域,邁出了從貼牌生產到自主品牌轉型升級的重要一步。
然而,人力成本是關鍵,要順利實現轉型升級,還需要大量能夠操作設備的、高素質的產業技術工人。
“通過‘機器換人’,在插件工序環節,原來需要800名員工才能完成的工作,現在隻需要60人就能完成。在人力成本減少的同時,公司的效益反而提高了差不多20倍。”何思模介紹。
這個所謂的“機器換人”,是廣東省在助推制造業轉型升級方面做出的大膽嘗試,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企業視為降本增效的有力武器。
如今,“機器換人”已經開始在東莞企業間大面積推廣開。數據顯示,通過“機器換人”,2015年東莞市工業技改完成投資額231.2億元,同比增長85.6%。減少用工43684人,單位產品成本平均下降9.82%。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意就是要解決經濟發展中遇到的各式各樣的問題,降成本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任務之一和關鍵環節,企業所能降的成本是企業內部的生產經營成本,不同的企業需要針對自己所在的行業去探索、去改革,因此,企業降成本必須精准發力。
此前,國務院印發的《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案》中就提出,經過1至2年努力,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取得初步成效,3年左右使實體經濟企業綜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較為明顯增強。
何思模通過“機器換人”有效提升勞動生產率和品質,減低成本,有利於企業騰出更多的資金投入到核心技術的研發,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的同時,也可倒逼員工積極學習技術,提高個人素質,促進員工的升級,從而獲得更廣闊的就業空間,並拿到更高的報酬。
當前情況下,要想有效實現“降本增效”貢獻自己的力量,需要政府和企業雙方同時發力,一方面,政府要多渠道化解企業轉型升級成本,從更深層次激發企業活力,“喚醒”企業發揮自身能動性加快轉型升級,另一方面,企業要勇於創新、敢於超越,在人才培養和創新領域取得更加驕人的成績,才能打贏這場持久戰。
隻有這樣,降成本才能給經濟發展帶來持續的動力,才能讓企業有更多的剩余資金用於投資、創新、轉型,實現國家經濟發展新的飛躍。

胡發文在安徽岳西可真算是個名人,他的事例常常見諸報端。
三年前,胡發文一家還因為兒子學業、女兒疾病的原因,住在危房裡,一貧如洗。
在新滸村,像胡發文這樣因病致貧、因學致貧的貧困戶佔到半數以上。雖然新滸村的貧困有目共睹,但該村生態環境優良,有以茶、桑、果、藥為主的農業發展基礎,而且地理位置上距離岳西縣城隻有十多公裡……新滸村的生態及地理優勢同樣也顯而易見。
如何在山水之間尋財富?2012年11月,新滸村幾位黨員帶頭成立了山水間種養專業合作社,通過流轉土地種植蔬菜、農作物,養殖水產家禽等。第二年,眼看著村裡不少鄉親們都進了合作社,在家門口就把錢掙了,胡發文也動了心。
因戶因人施策,針對他家情況,縣裡引導其將自家承包的2.4畝土地流轉入股到村裡的山水間合作社,並在合作社務工。因為懂一些水產養殖方面的知識,胡發文在合作社裡負責照管40畝魚塘。去年,土地流轉的分紅,加上在合作社打工的工錢,胡發文總共拿了35000塊錢回家。
“在家門口打工,不僅能顧著家,照顧子女,還能省不少開銷,這35000塊錢基本上就是我一年的淨收入。”胡發文憨憨地笑道,脫貧后我們一家人住進了三間二層的新房裡,目前家中彩電、冰箱、洗衣機等家電一應俱全,明年爭取把空調也給安上。
從掙不了錢、顧不了家的外出務工人員,到以“土地+人力”入股家門口大型農業合作社的社員,胡發文的脫貧之路也是這個岳西縣最典型貧困村的脫貧攻堅縮影。
據了解,目前山水間合作社共有社員210多戶,其中71戶為貧困戶,按照“合作社+基地+農戶”的發展模式,通過勞務用工、土地流轉、利潤分紅等,實現了年人均增收5000至16000元。
岳西縣由26年前的“通訊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治安基本靠狗、取暖基本靠抖”。到如今,大多數鄉村已經實現“走路不濕鞋、做飯不燒柴、吃水不用抬”,農村樓房率提高到80%,鄉村面貌煥然一新。

根據經濟學“木桶效應”原理,一隻木桶能裝多少水,是由其最短的木板決定的,隻有補齊短板才能增加容量。
在補短板方面,既補硬短板也補軟短板,既補發展短板也補制度短板,而貧困問題無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突出的短板。要堅決打贏扶貧攻堅戰,到2020年實現全面脫貧,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道路上,不能落下一個貧困家庭,丟下一個貧困群眾。
2016年是我國脫貧攻堅首戰之年。2016年12月10日,國務院扶貧辦主任劉永富在全國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上表示,預計全年減少1000萬以上農村貧困人口的任務可以超額完成,脫貧攻堅首戰告捷,取得良好開局。
據了解,去年中央和省級財政專項扶貧資金首次突破1000億元,其中中央為667億元,同比增長43.4%﹔省級超過400億元,同比增長50%以上,扶貧投入力度空前。
2017年是脫貧攻堅承上啟下、全面突破的關鍵之年。去年底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指出,進一步推進精准扶貧各項政策措施落地生根,確保2017年再脫貧1000萬人以上。
2017年脫貧攻堅工作的主要目標任務是在產業扶貧、易地扶貧搬遷、勞務輸出、教育衛生扶貧、貧困村集體經濟和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取得新進展。在扶貧責任落實、扶貧資金監管、社會力量參與、激發內生動力等方面取得新突破,在化解因病致貧返貧、保障安全住房、幫助特困地區特困群體脫貧等方面進行新探索。
“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脫貧攻堅戰的沖鋒號已經吹響,全黨同志務必拿出“敢教日月換新天”的氣概,鼓起“不破樓蘭終不還”的勁頭,向貧困發起總攻,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確保到2020年所有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一道邁入全面小康社會,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寫下新的光輝篇章。

人 民 網 版 權 所 有 ,未 經 書 面 授 權 禁 止 使 用
Copyright © 1997-2017 by www.people.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