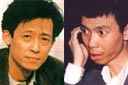一家隱匿於河北省青龍滿族自治縣重重山巒間的礦業公司,成為了河北鋼鐵集團涉嫌國有資產流失的証據所指,這是一個存在了近5年的秘密。
穿過長長的梯子嶺隧道,就是青龍縣的祖山鎮,然后沿著公路逶迤南去,道路的左側即是當地人熟知的廟溝鐵礦,它隸屬於河北鋼鐵集團礦業有限公司。
從外面看,這座鐵礦並無特殊之處,但從礦區中控室旁邊的一條道路斜坡而上,就可見一塊寫有“斯利礦業”的小牌子,挂在屋檐下。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調查發現,斯利礦業成立於2008年5月,其法定代表人為現年51歲的王義平,他乃河北鋼鐵集團董事長王義芳之弟。
眾多証據顯示,青龍斯利礦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斯利礦業)在這5年來,依傍河北鋼鐵集團的資源優勢,無償利用國有廟溝鐵礦提供的場地,並涉嫌借“利用尾礦”名義使用其原料礦來生產鐵精粉,謀取自己的利益。
盡管就在記者調查的3月26日,斯利礦業將其法定代表人匆忙作了變更,但已然構成的利益輸送以及謀利嫌疑,並不會因此而消弭。
就上述疑點,昨日(4月8日)晚,記者撥通了王義平留在工商資料上的電話,他知曉記者採訪意圖后,直接挂掉了電話。
斯利礦業突然變更工商信息
走進斯利礦業所在地,這裡已經停產。從水泥房內走出一個女人,阻止記者繼續前行。“停產好些天了。”她說。
此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所拍的視頻裡,這裡還是一派熱鬧的作業景象。“這幾年天天都開工,不知什麼原因這兩天停了。”對於礦區的一些工人而言,這樣的停產情況並不多見。對於停產原因,他們表示並不知情。
未過多時,一輛白色車子跟了上來,車上的人自稱是廟溝鐵礦的,問記者來自何處。之后他們一直尾隨,最后喊來了當地警察,試圖中斷記者的採訪。
工商資料顯示,斯利礦業成立於2008年5月,由自然人王義平、王雲海和何軍各出資700萬元(合計2100萬元)聯合成立,性質為私企。
記者掌握的《公司設立登記申請書》顯示,斯利礦業法定代表人為王義平,廠址位於祖山鎮廟溝鐵礦院內,經營范圍包括鐵礦石磁選、鐵精粉銷售、五金、機電、鋼材、建材、潤滑油脂、橡膠制品和機械設備等。
青龍滿族自治縣是冀東主要鐵礦集中區之一。斯利礦業所在的礦區屬於露天開採,斯利礦業實際上以鐵礦石磁選和鐵精粉的銷售為主。
近5年來,這家“棲身”於國有廟溝鐵礦內的企業,在王義平的主掌下,進行著秘而不宣的作業,就連廟溝鐵礦內的一些工人也不知情。像《安全許可証》這樣重要的証件,斯利礦業和廟溝鐵礦居然共用。出自2009年5月1日的一份“証明”中顯示,“斯利礦業和我礦(廟溝)共用尾礦庫,安全許可証廟溝鐵礦已經辦理。”
3月26日,記者在河北省工商局網站上能查到的注冊編號為“130321000002027”的斯利礦業,卻不見了蹤影。
同一天,記者在青龍滿族自治縣工商局查詢到,斯利礦業的法定代表人由之前的王義平,變成了王雲海。持股比例也發生了變化,王雲海持股1190萬元,何軍910萬元,王義平從股東名單上消失了。
此前作為法定代表人的王義平,緣何要在此時退出?
棲身國有鐵礦 場地無償佔用
據《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多日的實地調查,王義平在斯利礦業的退出或為“避嫌”,因為他的哥哥是河北鋼鐵集團董事長王義芳。
在王義平的老家平鄉縣王元村,多位村民証實了這一信息。
河北鋼鐵集團成立於2008年6月30日,是由唐鋼集團、邯鋼集團強強聯合組建而成的國內最大、全球第二的特大型鋼鐵集團。官網信息顯示,2010年初,集團掌控的鐵礦石資源達44億噸,子公司河北鋼鐵集團礦業公司擁有4個大型全資鐵礦,廟溝鐵礦是其一。
近些年,國有廟溝鐵礦效益不錯,2011年全年共完成採剝總量566萬噸,生產鐵精粉78萬噸,實現利潤5億多元。
在整個青龍滿族自治縣,廟溝鐵礦基本上是唯一國有鐵礦,縣礦業管理局一位負責人指著牆上懸挂的“選廠分布圖”說,除此之外,其他都是私有鐵礦。在這幅圖上,各個鐵礦的坐標都是單點分布,迥異的是位於右下角的廟溝鐵礦,在它的分布點上,也清晰地重合著斯利鐵礦的位置。
“斯利礦業並不是廟溝鐵礦的公司,而是由王義平等人在青龍縣注冊的私人企業。”縣礦業管理局辦公室主任向記者証實。
為何一家私有礦企與國有廟溝鐵礦的位置重合?一份由廟溝鐵礦於2008年6月10日出具的、由王義平和王雲海等3人簽字的《証明》顯示:“茲証明王雲海等人因出資組建青龍滿族自治縣礦業有限公司,無償佔用我單位土地,建年產10萬噸選廠一座……位於祖山鎮廟溝鐵礦院內,地上建筑物及構筑物、機器設備等資產為王雲海等人共同出資投入,產權為王雲海等股東共同所有,產權無爭議。”
隨后的一周內,當時的唐鋼礦業有限公司(現河北鋼鐵集團礦業有限公司)給青龍滿族自治縣工商局出具的一份《經營場所使用証明》中稱,同意將廟溝鐵礦院內的120間房屋計1578.18平方米,場地7000平方米用於開設斯利礦業。
一個月之后的2008年7月18日,廟溝鐵礦向縣礦業管理局提交一份《與青龍斯利礦業公司合作建廠提高鐵精粉生產能力的申請》,提出引進斯利礦業與廟溝鐵礦合作,新建一座年產10萬噸鐵精粉的選礦廠,總投資2100萬元,廠址在廟溝鐵礦院內。
“利用尾礦”實為使用好礦?
至於合作建廠的由頭,上述申請材料作了說明,“隨著我國鋼鐵工業的發展,鐵精粉市場日趨緊張,致使廟溝鐵礦煉鐵用的原料鐵精粉採購困難”,所以希望“依托廟溝鐵礦現有資源,完全利用廟溝尾礦庫,提高鐵精粉生產和自供能力。”
發出申請之后,縣礦業管理局給出了“同意”二字。斯利礦業開始在廟溝鐵礦院內進行生產,所用資源基本上都是依托於廟溝鐵礦現有資源。
對於提及的 “完全利用廟溝尾礦庫”,據了解在實際中並未完全執行。近5年裡,斯利礦業一直宣稱利用尾礦進行鐵精粉生產,可真實情況一直受外界質疑。
斯利礦業鐵選廠 《建設項目環境影響報告》指出,“建設年處理鐵礦石為30萬噸,原料礦由廟溝鐵礦供給,礦石品位為30%,年產10萬噸品位為65%的鐵精粉。”在其后的“原料用量”方面,特別指出“鐵礦石由廟溝鐵礦供給,自行運輸”。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梳理公開資料發現,作為露天礦區的廟溝鐵礦,其地質平均品位全鐵為30.16%,與斯利礦業在前述影響報告中所稱的礦石品位基本一致。
但是,前述《建設項目環境影響報告》中的說法,與之前廟溝鐵礦給縣礦業管理局的申請中提及的“利用尾礦庫”說法相左。那麼,斯利礦業到底有沒有使用廟溝鐵礦的資源?
“斯利礦業這些年來都在使用廟溝鐵礦的礦產資源,不能說連一點都沒有使用,我們這是實話實說。”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採訪的一位工人指出。
早在2010年3月,有當地工人在廟溝貼吧內向公司領導發問,“廟溝鐵礦有人用車拉礦石,是你特批的嗎?”隨后有人回復稱:“人家那叫拉廢石,領導也是這樣說的。”
“我們使用的都是廟溝鐵礦品位在百分之十五十六的礦石,”斯利礦業負責安全保衛的王敏(音)表示,“低品位的礦石,廟溝鐵礦都選不上,所以扔掉了,我們斯利公司的設備簡單一些,因此從他們扔掉的礦石中選,有時十車中選不出一車。”
但這一說法很難自圓其說。河北鋼鐵集團礦業有限公司何佳霞所著的《廟溝鐵礦尾礦再選回收改造實踐》一文中指出,廟溝鐵礦磨選主體系統每年產生尾礦65萬噸左右,尾礦的鐵品位為6.2%。
這篇刊於2009年的文章又稱,“山上小選廠每年產生鐵品位7.5%,磁性鐵礦物含量為2%的尾礦3.5萬噸左右。”據記者調查,此處的“山上小選廠”即為斯利礦業。
為此,記者採訪了多位鋼鐵業內專家,他們表示,從6.2%的尾礦中再進行二次利用,實際回收價值很小,基本上都是二氧化硅、氧化鋁等物質。
廟溝鐵礦15%左右品位的礦石是否如王敏所言被扔掉?何佳霞在上述文章中稱,廟溝鐵礦早就通過盤式磁選機對尾礦進行回收,“每月可回收大量品位為15%的粗礦粉。”
昨日(4月8日)下午,王敏在電話裡向記者又稱,斯利礦業在前期使用的就是廟溝鐵礦的高品位礦石,后來就不用了。至於具體時間,他已記不清楚。
有律師向記者表示,“鑒於斯利礦業法人代表王義平與河北鋼鐵集團董事長王義芳的兄弟關系,此事涉嫌利益輸送。”
如今,這些露天礦石資源日漸被開採殆盡,在2012年上半年,廟溝鐵礦開始了地下開採的前期工作,未來斯利礦業的原料需求是否還會依附於此,尚不得而知。
王雲海還有一個“斯利礦業”
變更了法定代表人之后的斯利礦業,何時開工還不得而知。
事實上,斯利礦業的企業稱謂,並不為其獨有,在毗鄰的遷安市,也有一家同樣以“斯利”命名的礦業公司,早在2000年10月16日成立。從遷安市工商局調出的資料顯示,這家企業的經營范圍也與青龍斯利礦業有限公司基本類似,也為鐵精礦粉磁選等,王雲海的發跡由此起步。
王敏告訴記者,現在青龍滿族自治縣做礦石營生的人,大多來自於遷安。在行業裡浸淫多年的王雲海也不例外,2008年與王義平、何軍三人在青龍成立了斯利礦業。
擁有兩家相同名稱的礦業公司,是否存在資源共享的情況?在王敏看來不存在這種情況,遷安斯利礦業公司所需的原料均在當地採購完成。
“遷安的礦石儲量大,但是瀕臨枯竭,所以在價格上比青龍縣高一些,這樣青龍當地的鐵礦大量被運到遷安以賺取差價,有時候每噸可賺二三十元,好的時候七八十元。”當地一位常年倒賣礦石的業內人士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
目前無從得知王雲海執掌的兩家“斯利”公司之間是否有依托國有礦產資源謀取“差價”之嫌。但是,青龍的斯利礦業和河北鋼鐵集團千絲萬縷的關系,卻是不爭的事實。
記者從獲得的數份斯利礦業的財務報表上獲知,其營業收入2008年為1487萬余元,2009年為4134萬余元,2010年為5356萬余元。僅這3年,營業收入就累計超過1億元。
就上述疑點,昨晚,記者撥通了王義平留在工商資料上的電話,他知曉記者採訪意願后,直接挂掉了電話。隨后記者多次撥打均是如此。(來源:每日經濟新聞)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發表成功!請登錄后盡快修改密碼。
發表成功!請登錄后盡快修改密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