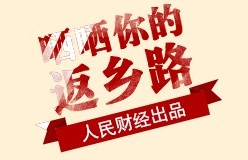|
|
北京市延慶縣張家營鎮胡家營村的“春晚”熱鬧上演,村民們自娛自樂,豐富春節文化生活。 |
 |
|
重慶市大足區通遠村,“壩壩席”廚師在忙碌。“壩壩席”是當地民俗,逢過年過節等招待鄉鄰親友。 |
 |
|
春節剛過,雲南省羅平縣臘山街道大水塘村的農民就忙著在田間澆水整地。 |
編者按:家鄉的自然風光、風土人情……是每個人記憶中最美麗的底色。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家”不同,每年的春節回鄉之旅,對常年奔波在外的記者來說,都是一次新的體驗,城市與鄉村的互動、豐收背后的喜憂、農民生活的變遷,這些看似“老套”的主題,其實恰恰最有“味道”,最值得咀嚼。因為時代大潮裹挾下的鄉村巨變,就蘊藏在這點點滴滴之中。
鄉村公路已經硬化,打工收入幾成農家全部收入
看南埂村
“城鄉一體化”
本報記者 高雲才
霧靄,把鄉村的天空拽得很低。此起彼伏、時斷時續的新年鞭炮聲,把安徽省安慶市大觀區海口鎮南埂村引入了馬年的第一天。傍晚時分,記者走進了幾個農戶的家,同村民們聊起了他們對“城鄉一體化”的期盼。
鄉村公路雖是硬化路,但想錯車太難了
村民吳強盡管已經年近半百,但因為長期在沈陽打工,思路蠻清楚。
“城鄉一體化?搞不清楚哪一年可以最終搞成,鄉親們倒是很盼望的。”老吳說:“老鄉們看得到的變化,是實實在在的。”
首先是路。
過去,村子裡一下雨,路就沒法走,到處是泥。現在,路修到了家門口,雖然是石子路,但畢竟下雨天走路方便了。村子裡的石子路連著鄉村公路,但鄉村公路有一個缺陷,雖然是硬化路,可隻有一輛轎車那麼寬,想錯車太難了。
其次是水。
村民過去吃水,要麼到鄰近的長江裡去擔水,要麼到附近的溝塘裡取水,因為水不太干淨,所以,講究點的村民就用明礬淨化后再吃,不太講究的村民,等水稍微沉澱變清后就吃。南埂村在圩區,過去吃水,常吃到有血吸虫的水,不少人患上了血吸虫病。現在,大觀區在南埂村附近修建了自來水廠,城鄉居民共用“一管水”,村子裡家家戶戶都安裝了自來水。
再就是合作醫療和新農保。
過去村民見到最多的人是“赤腳醫生”,現在村裡有了衛生所,更重要的是,農民有了新型合作醫療。平時繳點錢,看病的時候有國家補助,還能報銷一大半。另外,新農保也讓農民養老有保障。
“城鄉一體”得有個過程。初看,以為南埂還是原地踏步,但仔細想想,確實,“城鄉一體”讓村民享受到公共服務的陽光。村民有很多新願景,比方,垃圾圍村沒有解決,住房沒有新的規劃,小學校的師資有待補充……
打工收入幾成農家全部收入,為了生計一家人不能常在一起
分田到戶時,他春(化名)家是4口人,人均分田1畝左右,一年種一季棉花,一季小麥,輪作油菜和玉米,復種算上,1畝地收入滿打滿算也就是2000多塊錢,孩子要念書,家裡的房子要新蓋,老人要養……他春處在“收入飢渴”之中。
因為地裡種不出多少錢來,他春開始學布花編制手藝。10年前,師傅介紹他去西安搞布花編制,一個小作坊,他帶領媳婦和兒子,沒日沒夜地干著。靠信用贏得市場,也贏得了收入。他的小作坊,現在每年的收入是10萬元,比在家種地強多了。現在,他全家已在西安安營扎寨,還在郊區為兒子按揭買了套小房子。
除了市場時好時壞外,最令他不順心的事是,經常有一些部門以辦這個証那個証為由來罰款,要正規發票就罰得多,開個收據或不要發票就罰得少。所以,為了維持生計還得忍氣吞聲。
同他春經歷相差無幾,南埂村2000多適齡勞動力大部分都在外打工謀生。地,轉包給別人﹔轉包不出去的話,就撂著荒。雖然心痛,但也沒什麼好法子。正因為如此,打工收入幾乎成了南埂村村民的全部收入。村民打工的年淨收入水平不低,平均線都超過1.5萬元。
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南埂村“打工經濟”漸成氣候。平時,村子裡青壯勞力都不見了,因為過春節,再遠的路,打工的村民都要回家看看。他春說:“其實,家裡已一年沒人住了,但在西安,總不認為那是自己的家,南埂才是。”
望著即將擦黑的天空,他春說,很多打工的家庭有一個心病,為了生計,這個城市一個,那個城市一個,搞得一家人不能在一起。假如夫妻不在一起,兒女不在一起,還是很糾結的。
從庄稼漢到職業農民,糧農訴說豐收背后的喜與憂
噸糧田離咱
有點兒遠
本報記者 趙永平
喜:耕牛下崗,鐵牛上崗,種地越來越輕鬆
挂燈籠,拉大紙,貼春聯,年三十這天,堂叔武學玉一家忙碌著。在山西壽陽縣立元村,武學玉算個精明人,當過30多年村干部,種地也是把好手。
“今年收成不錯,畝產上了1600多斤!”寒暄幾句,堂叔指著院裡堆得小山一樣的玉米說,過完年就能賣了,照現在行情,一畝穩賺1000多塊。
“過去城裡人叫咱‘庄稼漢’,現在是‘職業農民’。”同樣是種地,武學玉覺得最大變化是輕鬆了:“耕牛下崗,鐵牛上崗,政策實惠,糧價得勁,我種的25畝玉米,總共干不了2個多月,一年能收入2.5萬元,掙得不比在外打工少。”
這幾年糧食連年豐收,武學玉認為關鍵是邁了兩大步:
第一步是良種。五年前,愛趕時髦的堂叔用上先玉335種子,通過高效密植,每畝從300多株增加到4400株,“這品種抗倒伏、成熟好、脫水快,當年畝產就翻了番。”
第二步是農機。2012年他享受國家農機補貼,買了一台小型拖拉機,配套了旋耕機、點播機等農具。60多歲老漢學開手扶拖拉機,老伴天天提心吊膽,“最擔心走下坡路,剎車是反方向來的,有一次差點兒開到溝裡。”可老漢有股不服輸的勁兒,終於學會了開拖拉機,旋耕、點播等新技術落戶田間,畝產噌噌往上躥,一畝地頂過去兩畝地。
憂:基礎薄弱,先進技術看得見摸不著
雖然用上了新技術,武學玉覺得差距還很大:“縣裡南鄉那些地,玉米都是噸糧田了,在電視上看到東北不少地方,畝產能到2500多斤,咱家的技術在人家那裡早過時了。”
先看種子。“現在買種子有點像撞大運,心裡沒底。”堂叔說,這兩年先玉335有點退化,可再選什麼種子?東北種子產量高,拿來能不能適應?咱這兒有啥新品種?現在這些問題沒地方去問,隻能聽經銷商吆喝。堂叔回憶上世紀70年代,那時年年都搞試驗田,組織大家參觀學習,現在都沒了,這些年連農技員都見不到了。
再看農機。堂叔說,人家是大馬力機器旋耕,一下去就40多厘米,深耕深鬆,產量肯定高,咱小型農機比不了。另外,人家是平原地區玉米收割機,在咱丘陵山區不適應,收一次丟的太多。
還有基礎設施。村裡的1400多畝地,全都是靠天吃飯。堂叔說,30多年村裡沒有來過農田基礎設施項目,這幾年總的來說年景好,可一旦遇上個大旱年,就隻能干瞪眼沒招了。
武學玉年年從電視上看中央一號文件,尤其是關心有關糧食的政策,但他覺得電視上說的政策有的沒有享受到,比如良種補貼、科技推廣、測土配方等等,他常這樣寬慰自己:“咱這裡不是糧食主產區,也許有的政策咱這就該沒有。”
說起今后怎麼種地,武學玉覺得還是要多琢磨合作社,“我和你嬸兒年紀大了,再過幾年地裡的活就干不動了,孩子們都在城裡安了家,加入合作社能省不少心。”但想法和現實之間還有差距,村裡前幾年成立過種植合作社,沒干多長時間就黃了,一是因為農民想法難統一,二是山丘區地塊分散,像他家的25畝地,分了近20多片,小的隻有幾分地。
孩子們幾次想接他們進城,但兩口子都不想去。武學玉說,現在農村政策越來越好了,新農合、新農保,農民負擔輕了。他說:“攆上人家噸糧田,還有好多新技術要琢磨,不緊緊跟上,咱就該下崗啦!”
春節壓歲錢、婚宴紅包四五年翻番,讓親戚無奈感嘆
親情可貴
壓力不小
本報記者 顧仲陽
一年到頭,走親訪友﹔多年不見,同學好友小聚……這些都是人之常情。給小孩發壓歲錢,500元起步,婚慶紅包三五千元,稀鬆平常……很多農民甚至工薪階層,都坦言人情可貴,壓力不小!這是記者春節回浙江老家的一個最大感受。
壓歲錢500元起步,年終獎根本不夠過年送人情
大年二十八,剛回老家,就有兩個小學同學找我小聚。還未入席,同學見到我3歲小兒,每人掏出一個紅包,每個厚厚一沓,1000元的壓歲錢。很單純的同學聚會,給1000元壓歲錢,難道是老同學有求於我?飯桌上,不禁嘀咕。飯桌上敘舊閑聊,直到酒散人走,未提任何幫忙的事。
送走同學,馬上問我哥:怎麼給這麼多?
我哥笑笑:“我們這裡的壓歲錢現在基本上都是500元起步,稍微年輕的長輩給小孩1000元壓歲錢,很正常。”
我記憶中拿過的壓歲錢最多是100元,大概是我10多年前上大學時。上次回老家,還是四五年前,記憶中發的壓歲錢一般也就兩三百元。由此推算,四五年翻一番。
“壓歲錢漲得真快,遠遠跑贏收入增加啊!”
“是夠快,平時壓力也不小!”在事業單位上班的哥哥告訴我,這些年老家的人情錢一直飆漲,特別是“十一”黃金周、春節期間,辦喜事的特別集中,“十月份我的工資經常不夠送人情,春節期間年終獎根本不夠用,還得搭上一年到頭省吃儉用省下來的錢。”
見到三嬸,是在小叔兒子的婚禮上。剛一落座,見到我兒子,長輩們又爭先恐后的發壓歲錢。紅包一個比一個大,真的沒有少於500元的。
席中,三嬸過來把我拉到廳外一個角落。拿出200元壓歲錢,很不好意思地解釋:三叔身體一直不好,家裡沒多少收入,頭一次見到我兒子,不好意思隻能少給點,聊表心意。
“心意我領了,紅包就別給了。”我執意不收。推來塞去幾次,三嬸開始紅上了臉:“你不拿,就是嫌少,就是看不起叔嬸!”
降低婚禮費用非常困難,份子錢自然水漲船高
我留意了一下小叔家的婚宴開支。
小叔告訴我:“今年你弟喜酒小辦,隻請了我的同輩和一些至親。”婚宴隻有四桌,確實規模不大。我看后頓覺小叔這樣挺好,響應中央號召。但一看上的酒菜,一點不低調。一大堆生猛海鮮,10個人30來個菜,盤子堆得三層高。一結賬,一桌4000來元。酒席辦兩餐正餐,人均消費就得800元,再加上別的開支,人均人情少於1000元,叔叔確實得貼錢辦。
普通百姓過日子,不精打細算不行。辦個喜事也不能大把貼錢,影響正常生活,這是大家的共識。怪不得一看禮簿,份子錢沒有少於1000元的,五千,上萬的都有。
看來,要降份子錢,還得從降低酒席費用著手。飯后問小嬸,有沒有辦法降下來?“我也想啊,可是實在沒什麼好辦法!”她笑著搖頭:自家辦省錢,現在大家多數在城裡買了商品房,辦酒席哪有那麼大場地、那麼多餐具?春節期間辦,菜市場上絕大多數菜價比平時都漲了五成以上,費用肯定更高,可也就春節,能讓親朋好友們湊得齊整點。“好在這些年時興打包了,這些剩菜全家過年綽綽有余,放在以前,浪費更大!”
人情可貴,但人情要是成了負擔,也就變了味。“如果能借著這次中央轉作風,能把人情風也轉轉,自然大家都歡喜。可這麼多年形成的傳統習慣,不是說轉就能轉的。退一步想開點,也沒什麼大事,人情嘛,終歸有來也有往。”哥哥的話挺有道理。
《 人民日報 》( 2014年02月09日 09 版)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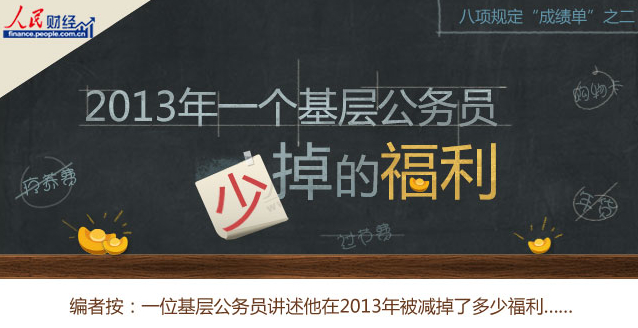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