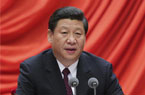这个时代似乎缺乏生命的沉重感
陶国璋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哲学教授,他教授的《死亡与不朽》课程已经开课20多年。他课上的学生比王一方的更年轻,大都是刚上大学没多久的本科生。每次一上课,陶国璋看着台下年轻的面孔,都会开玩笑地跟他们说:“大家怎么这么想不开呀?你们才这点年纪,就都跑来学习死亡了?”
跟其他死亡课老师不太一样,陶国璋教授这门课跟自己的经历有很大关系。他7岁的时候就患上肾病,39岁那年又动了肾脏手术,被疾病折磨许多年,“有好几次跟死神打了声招呼”。
因为生病,陶国璋常常一个人在医院养病。在那时候,他看了好多死亡主题的电影,阅读了许多关于死亡的哲学经典。他读到了尼采的话,“如果一个人在世界找到一个活下去的理由,他就能够面对任何的困难。”所以直到现在,碰到跟死亡有关的新闻,他还会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要活下来,为什么不能放弃。
让他意外的是,当他回到学校教书,发现那些健康的年轻人,竟“对价值有一种失落”。他们动不动就放弃,有的因为情绪波动就放弃考试,有的没读完大学就坚持要退学。
陶国璋说,年轻人的放弃让他很担心。“每个时代的人都会死,但我们这个时代却似乎缺乏生命的沉重感,我想年轻人这么轻易地放弃了各种丰富的生命体验,跟他们对于自我价值的理解有关,生命似乎轻得着不到地。”他说,“死亡其实是‘生的局限性’,是生命的参照物,不理解死亡,就难以找到生命的价值。”
于是,陶国璋在统共13节的死亡课里,邀请不同背景的人,讲述自己视角下的死亡——佛学研究者讲述佛家的死亡,医生跟学生讲“什么才算好死”,甚至还有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在课堂上跟学生分享真实的案例。
“宗教对于死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在通识课讲死亡,我还是更希望用不同角度,增加他们对这个话题的思考。”陶国璋说。
在复旦大学,同样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胡志辉,开了一门叫做《生命教育研究》的课程。2005年开课时,几乎每个人都会过来问:“什么叫生命教育啊?”
胡志辉说,他追求的是“生命化的教育”。他上课的方法很特别——学生做主导,由他们自己去挑,要讲什么话题。
在几次课上,学生主动提出,聊聊死亡。在一个坐了20人的小教室里,学生们自己站起来讲讲,自己生活中曾经遭遇的死亡——哥哥自杀,同学跳楼,亲人辞世。
“在我的课上,我不讲理论,主要让学生自己去分享人生经历。我觉得对一个人影响最大的是他自己的人生经验,所以在这样的课上,我们分享彼此生命中沉重的人生体验,看到人性的丰富多彩,相互分担。”胡志辉说,“这样不会告诉你一个答案,告诉你该如何承受死亡,但通过看到不一样的生活,丰富了我们自己的生活,让我们多点对生命的理解。”
尽管如此,零星的死亡讨论还是略显单薄。虽然胡志辉也想多讲讲关于死亡的话题,但是由于他的课程奉行“学生主导”,所有话题都是学生选择的,所以,超过一半的话题都是“爱情”,只有星星点点的几节课在讨论“死亡”。
“看来,爱情比死亡更坚强。”胡志辉调侃地说。
失去了让死亡“脱敏”的故事后,我们对死的恐惧,其实变成了对生的恐惧
王一方也喜欢让学生自己讲故事。比如讲到人类学视角下的死亡,他就会请农村来的同学,给大家讲讲村里的死亡故事。
在他的记忆里,在农村几乎每个月都能碰到“村头故事”——村子里有人去世,家里人会在村头办丧事,有人敲锣打鼓,戏班子搭台唱戏,亲人披麻戴孝跪在周围,晚辈去磕头,乡里乡亲去随点份子钱,送逝者一程,最后村子里的人聚在一起,唱大戏,放鞭炮,热热闹闹地吃一顿大餐,算是向死者告别。
所以,村庄里的死亡并不完全是一件悲痛的坏事。通常情况下,如果丧事办得好,家里人还会感到安慰和满足,“走得挺风光的”。
王一方发现,一说起这些“村头故事”,来自城里的学生都不怎么说话,“看上去都挺惭愧的”,因为他们住在城里的单元房里,有时候隔壁房间有人去世,他们常常过了很久都还不知道。
“村头故事对于我们每个人,是一种‘死亡脱敏’。它告诉我们,‘死亡就是夜幕降临’,‘回到祖宗的怀抱’,没什么好害怕的。我们当下之所以恐惧死亡,是因为死亡被现代医学恐怖化了。一想到死亡,就是躺在ICU里痛苦地插着管子的样子,每一口呼吸都消耗大量金钱,每一秒心跳都可能导致亲人倾家荡产。”王一方说,“失去了村头故事后,我们对死的恐惧,其实变成了我们对生的恐惧,对家庭经济的恐惧,对人伦关系的恐惧。”
这位哲学教授感叹:“村庄的沦陷”让死亡成了“躲在暗房里尚未感光的思想底片”,“我们失去了‘村头故事’,也失去了直面死亡的通道,失去了思考、理解它的‘感光机会’。”
为了让死亡“感光”,陶国璋也在课堂上鼓励他的学生去参观殡仪馆,到解剖室触摸尸体。一开始只是课堂建议,结果没人去;后来他给这个参观加了一个学分,还是好多人不愿意去;最后,陶国璋“掌握了上课技巧”,立下规定,要么参观殡仪馆,要么写读书报告。结果,“学生们都去抢到殡仪馆参观的巴士座位了”。
“我告诉妈妈上课要去参观殡仪馆,结果换来她的质疑,‘这是什么课?这地方有什么好去?’”陶国璋的学生在参观后写信给他说,“可我到了才发现,光是棺材就有不同价格、不同年代、中式或者西式的、购买的时候一次结清还是分期付款,原来死亡也有这么多讲究。”
陶国璋发现,年轻人其实对死亡很好奇。有次上课上到一半,他带着学生到距离教室不远的解剖室参观,本来想着待上十几分钟就回教室,结果一下子待了45分钟。原本以为学生们会恐惧冷冰冰的尸体,但他们却真的伸手去触摸实验室里的解剖样本,还团团围住管理员,好奇地问各种问题——这些供实验室解剖的遗体都是哪些人捐赠的?捐献的遗体能做什么实验,有什么用?
当然,也有学生不能接受这样的课程。“我要是知道得去殡仪馆,我可不选这门课了。”一个上过《死亡与不朽》课程的内地学生说,“我当时选这门课,可全是因为它不用做Presentation(课堂报告)啊!”
不过,这个避讳谈及“死”的学生直到现在都还记得,在课堂上第一次看到电影《入殓师》,了解到死亡之后还有许多庄重的仪式。虽然直到现在他还是会把“殓”字念错,但他说,这是他第一次知道,“原来死亡不是终点,后面还有这么多故事”。
 |  |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