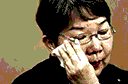海南电网文昌供电局昌洒供电所韩海雄:救另一个灾
见到林海霞的时候,她正和韩海雄80岁的老母亲坐在安置房里发呆。这里是她们娘俩临时的居所。林海霞是文昌供电局昌洒供电所配电班班长韩海雄的妻子。家里的瓦房被“威马逊”掀翻后,所有的家具和电器一起泡了水,林海霞和婆婆二人被安排到安置房住下来。然而,即使是这样,台风登陆后,韩海雄也一次都没回家救过灾,因为,他要救另一个灾。

海南电网文昌供电局昌洒供电所韩海雄
海南省文昌市昌洒镇作为本次台风受损重灾区,绝大部分的电力设备都被摧毁。从7月18日起,韩海雄就和同事们一直奔波在抢修一线,他的家,距离昌洒供电所不过几公里。就在抢修的这些日子里,他不下5次地经过家门口,却从不曾靠近一步。就连家里坍塌的消息还是妻子托别人转达给他的。
他告诉笔者,这些天以来,“家”这个概念只在他的脑子里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得知家里塌了,一次就是这次的采访。“不是不挂念,是根本没时间挂念。”昌洒供电所包括所长在内就只有16名员工。当将近1600人的外援抢修队伍进驻昌洒这个小镇,抢修和后勤物资源源不断地涌入,所里几乎所有的员工都必须承担起后勤、引路、卸物资的责任,人手紧缺的情况下,50岁的韩海雄也就把自己当成了20岁的小伙子用,经常忙得一晚上只能睡3个小时,更别提有什么抢修之外的念头了。
“我知道我对不起她们,但是90%的百姓都没电用,我心里着急。”这位在电网干了一辈子的老员工眯着熬得干红的双眼,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还记得前些天,一批物资从海口运过来,大半夜才到昌洒。卸货的任务一下,睡得迷迷糊糊的韩海雄立即从床上爬起来,跑向所门口。近百斤的物资堆在车上,他与同事得一箱一箱地往外扛。50岁的他毕竟不是小年轻了,体能消耗得很快。可他知道,百姓的光明都指望着他们。那一夜,他与同事一直忙到凌晨5时,回洗手间洗了把脸,换上了前天的衣服,又骑着摩托车出门干活去了。
当这次采访临近结束,笔者问韩海雄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时,韩海雄几度张口,话还没来得及说出,就又被他吞了回去;最后,他像是下定了决心一般:“你回去的时候会经过政府安置房那儿吗?能帮我看看我老妈跟老婆吗?我妈年纪大了。”
凑巧的是,当离开林海霞与韩海雄的老母亲住的安置房时,婆媳俩也拜托笔者帮忙捎句话给韩海雄:“我们一切都好,你放心吧,安心抢修”。(习霁鸿)
广东电网清远清新供电局何志刚:“哪里最艰苦,我就去哪里”
何志刚是清远清新供电局配电运行专责,7月21日下午,由于扁桃腺严重发炎,他正在医院输液,接到通知后,他拔掉针管,匆匆回家收拾几件换洗衣物,就随抢修车连夜赶赴海南海口。
22日,到达海口后,何志刚立即忙于组织抢修工作的开展,一直忙到深夜,准备休息时,拿出手机,16个未接来电,全部来自家人,“一直忙着抢修的事,忘记向家里报平安,孩子和他妈肯定是担心我的身体。”家人的关怀,触动了这位“保电先锋”心中最柔软的角落,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广东电网清远清新供电局何志刚
台风过后的海南,太阳直射在身上,有如灼烧,衣服瞬间湿透,何志刚望着被台风席卷过的文昌,看着地上倒落的低压电杆,顾不上擦汗,又埋头开始抢修。何志刚完全将医生关于注意饮食和休息的嘱咐抛于脑后,连续多日没日没夜地拼命苦战。
白天,他坚持战斗在最困难、最紧迫的抢修一线,协调小组内的抢修、后勤的大小事务;晚上,集中开会、商量下一步的抢修工作计划。海南艰苦的抢修工作使他变成另一个人,又黑又瘦,两眼深陷,嘴唇干裂起泡,病情也加重了,大把大把吃消炎药。队员们都劝他休息一下,他始终不听劝,“九头牛都把不能把他从前线拉回来”。
今年50岁的何志刚,个子不高,结实、憨厚,黝黑的脸上刻着长期从事户外工作的风霜,在同事心中,他是一位亲切和蔼,干事兢兢业业、认真踏实的前辈。
自从1981年入职以来,他参加过20多次抗灾复电战斗。他总打趣说自己是“劳碌命”,一有抢修任务就坐不住,“哪里最艰苦,哪里最危险,我就想到哪里去,抢修前线对我有着说不出的魅力。”(何淑文)
深圳供电局陈汉邦:跳进粪池捞导线
“洗了5次澡都还是觉得臭。”陈汉邦是深圳供电局700多名抢修队员里的一员,回忆起长流1号线砖厂支线的抢修,表情十分复杂,“导线掉进了池塘里,和水草缠在一起,我们不得不下池塘”。
与其说那是水塘,不如说是污水池。“旁边就是养猪场,猪粪连同鸡粪鸭粪都往这里倒的。”现场负责人张仁喜说,“齐胸的水,最深的地方还没过人头。”
陈汉邦今年48岁,瘦高瘦高的,皮肤晒得黝黑。7月22日在深圳做完两单抢修的活儿已经是晚上7时,接到任务后,他和同事们一道收拾工器具,23日凌晨3时驱车前往海口,当天下午5时左右赶到工地就立即展开抢修,一直忙到24日凌晨1时多。
“那天收拾完工具回到酒店快4点多了,稍作休息,8点多又赶回工地接着干。”陈汉邦说,“光第一天就爬了4个杆。”

深圳供电局陈汉邦
深圳是全国电缆化率最高的城市,虽然每年都有爬杆培训,但毕竟只是一年几次。陈汉邦是这次能登杆作业的兄弟中年纪最大的,却是上杆最频繁的。“他最长一次在电线杆上呆了快12个小时。”张仁喜说。
光站在室外就觉得要被烤焦了,很难想象陈汉邦是靠什么支撑下来的,而且他还不是简单地呆在那儿。
“爬上杆后,要往上拉导线,一直抬上横杠,最后组装金具。”陈汉邦说,“导线越往上拉越重,最后25公分左右,几乎要200斤的力,只能靠肩膀抬上横杠。”
一般一个人每天登两次杆,体力已经到极限了。可陈汉邦已经记不得,这几天究竟登了多少次杆,拉了多少导线。“看到居民用上电的那一刻,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他说。(朱婷婷)
广东电网中山供电局林川:“单枪匹马”送物资

广东电网中山供电局林川
“喂!有6辆车先出发,后面还有11辆陆续分批出发!不能等,装好一辆出发一辆……”
“我们这边有两台车抛锚了!没事,保证能完成任务!喂!这里信号不好,你大声点……”
“司机大哥,您别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
7月23日晚凌晨4时,前往海南的高速公路上,6辆40吨大卡车的低沉马达轰鸣声回荡在整个夜空,车上装载着中山供电局连夜从广东调配前往海南抢险救灾一线的15米电杆,一位年轻的小伙子一手拿着电话,一手拿着对讲机,大声地呼叫着,他就是林川,中山供电局物流中心合同执行员,也是这批多达300件、重达600余吨的救灾物资运送负责人。就这几天里,他以大货车为家,以路边的石板地为床,连夜押送供电物资赶往海南省海口市。
林川告诉笔者,从中山出发到海南一路上可谓是险情不断,现在回想起来都有点后怕,带着这么大一批货,如果中途出了岔子怎么办,连夜赶车出现安全问题怎么办……
刚到清远,问题就接踵而至了。供应商告诉林川,大货车是有,但不是专用的电杆运输车,是那种拖头拖着的平板车,电杆是圆的,车的平板载台根本无法固定电杆啊。林川灵机一动,在平板载台两侧加装钢柱不就可以解决了吗?问题解决了,他就浩浩荡荡地带着17辆大吨位的大卡车前去附近的汽车修理店,焊接安装钢柱。一直弄到23日凌晨一二时,紧锣密鼓地就开始吊杆、装货,凌晨3时,第一辆装载完毕的车辆出发。
这时候情况又出现了,同行的同事突然家里有急事,务必要赶回中山,经请示后,林川成了这批物资唯一的负责人,一下子成了“单枪匹马”了。林川当时也没多想,事后他说,一个人带着这么大批货,其实风险性是很大的,但在那种环境下只能顶着上,前线都在等着电杆呢!
没过多久,麻烦又来了。凌晨4时左右,有两辆车抛锚了,一辆爆胎,一辆钢柱焊接处爆裂,而这时已经在高速路上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真的是急死人啊!而最糟糕的是,司机大哥们因为连夜开车已显疲倦,有点“罢工”的迹象,言语变得烦躁不安。林川明白此时急也没用,一边不断安慰司机大哥们,一边打高速救援电话,询问附件有没有汽车修理店和休息站。终于,在救援人员的协助下找到了修理店,林川还跑到休息站买吃买喝地给司机大哥们,好话说尽,磨破了嘴皮子才安抚好司机大哥们。
23日上午10时,首批6辆车到达湛江徐闻渡口登船渡海,其余11辆也在第二天24日上午9时到达,林川那个晚上便是在渡口的候船室板凳上睡了一晚。24日正午12时,这批救灾物资终于顺利送达海南抢险一线。至此,林川已经连续作战三天两夜了! (刘文浩)
贵州电网贵阳供电局童得全:突击队里的“精算师”
在贵阳供电局驰援海南抢修保电现场,有一名突击队员被大家尊称为“精算师全叔”,他有这样的尊称,并不是因为他年纪大,而是因为他经验丰富。全叔,全名童得全。
7月25日,全叔所在的突击队中被分成6个小组开展核查,共18个台区的核查数据,全部归口在他那里,由他进行分析统计,然后报给指挥部,以便协调抢修物资。
“10千伏公坡主线龙跃公变电杆、横担不缺,但需要调4付螺栓、2只延长挂环以及2只绝缘子……”测算后,全叔在材料明细表中,一一做好记录。
然而,仔细一瞧,这记录其实并不好做。在办公桌上,横七竖八摆放着多张纸条,纸上圈圈点点,画满了线条以及潦草的字迹。有的纸条画得像八卦图,有的像蜘蛛网。全叔说:“这些纸条的字迹来自于12个人,哪一张是谁写的,我一看笔迹就能知道。没办法,如果连笔迹都不能认清,这工作没法做。”
“复电需要施工,施工没它可不行。”全叔所做的工作,不能大意。需求物资如果申请数量不够,突击队队员只能干瞪眼。还有一种情况,物资有准备,但型号如果不对称,同样用不上。

贵州电网贵阳供电局童得全
在材料明细单中,可以看到,表格中列有线路名称、所需物品名称、型号、单位、数量等分项,根据日常使用情况,全叔一共列出了28项材料清单。对于物品的配置,全叔显得很有经验。他说,很多材料之间是相互衔接的,属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只有材料配备齐全,突击队员有劲才有地方使,抢险工作才能顺利推进。因此,虽然这项工作费时费脑,但值得认真做。”全叔说。
从25日上午10时开始,直至当日晚8时,全叔所负责分析统计的18个台区抢修复电材料明细单数据核算基本完成。这些数据被第一时间送达贵阳供电局驰援海南抗风保电指挥部,由指挥部集合其他突击队核算数据,统一协调相关单位调配物资,以确保抢险工作顺利开展。
与奋战在电杆、线路周边的一线抢修队员有所不同,全叔脸上少了大把大把的汗水,但心里却多了一分踌躇满志。(杨志坚)
云南电网楚雄供电局杨卓艳:“我还是在这里照顾大家”
“7月22日中午1点多接到通知才知道要走,没想什么拿了生活用品和药就走了。”50岁的杨卓艳是楚雄供电局职业健康管理专责,如今,她成为了海南抗风救灾的队医。到了海南文昌市翁田镇,云南电网公司参加抢险的1239名人员到齐后,杨卓艳发现自己是这个队伍里唯一的女性。
“没什么,我就住这里。”在24日上午8时进入翁田镇中心小学居住地时,大家犯难了。在一间幼儿园教室的狭窄空间里挤进了26个大男人,教室隔间成了杨卓艳的居所。这里既不通风又炎热不堪,杨卓艳拿了一块布做成简易窗帘。晚上,这种不隔音的窗帘根本挡不住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在这里,女士也无法享受一丝特殊照顾,杨卓艳和大家一样,忍受了36个小时无休无眠的车程,如今又要忍受缺水少电的困扰。指挥部为了照顾杨卓艳,让她外出找单间居住,但是杨卓艳拒绝了:“我还是在这里照顾大家。”
就这么个唯一的女队员,照顾着这个抢修队里1238个男人。
在云南生活惯了的队员,即使年轻,在高达36℃以上的高温天气下,中暑生病也难免。
7月25日中午,昆明供电局抢修队员杨晓禹满头大汗来到指挥部,进门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有个兄弟中暑了,我找一下医生。”此时,杨卓艳恰好外出买药。指挥部决定:立即将中暑队员榆梦飞送到卫生所。
几分钟后,外出买药的杨卓艳回到驻地,听说这一状况,拿起药箱顶着太阳立即赶往翁田镇卫生所。在卫生所,杨卓艳和卫生所医生充分交换了意见,决定打点滴治疗。经过简单治疗后,榆梦飞情况有所好转。第二天,榆梦飞又加入到抢修工作中。
当天,20岁的楚雄供电局抢险队员李光辉,从早上6时到晚上7时,整整抢修了13个小时,晚上发起了高烧,还伴有轻度中暑。
工作结束回到驻地后,杨卓艳为他开了退烧药,又让小李服下了藿香正气水。送小杨回到宿舍后,杨卓艳还在叮嘱:“一定要多喝水。”

云南电网楚雄供电局杨卓艳
同样年轻的楚雄供电局抢险队员杨哲懿,来到翁田镇后,由于气候的原因,患上了急性化脓性中耳炎。杨卓艳开了消炎药给他,并每天早晚两次为他清洗耳孔消炎。
25日,云南电网公司海南抢险指挥部将杨卓艳“调进”指挥部后勤组,今后每天她都要向指挥部汇报卫生防疫情况,她给出的建议在会上得到高度重视,在她的建议下,中暑预防和控制措施、传染病及日光性皮炎预防等知识在所有抢修队中得到普及,抢修队员健康得到了保护。 (樊家海)
广东电网珠海金湾供电局岑永源:“这家务活的奥妙多着呢”
在珠海金湾供电局援琼队伍里,有一个忙碌不停的身影,他不曾在杆上挥汗如雨,不曾在指挥中心帷幄运筹,却是整个后勤工作的顶梁柱,他就是珠海金湾供电局平沙所综合部主任岑永源,大家亲切地叫他“岑叔”。
刚到文昌,珠海金湾供电局抢修队伍驻扎的营地罗峰中学条件艰苦,宿舍卫生环境恶劣。趁着大部队去现场勘察的空档,岑叔抓紧时间带着几个年轻人把宿舍打扫了一遍。擦床板、洗厕所、拖地板,岑叔做得热火朝天。看着年轻员工有些手脚生涩,岑叔擦擦汗说:“这家务活看起来简单,里头的奥妙多着呢!”说罢又操起工具,一边干,一边给大家讲解示范一些小技巧。简简单单的一次大扫除,却让年轻员工受益良多。
搞完卫生的宿舍干净清爽,可是公司配给的各种生活物资尚未到位,岑叔喊来年轻员工,“走吧,我们买东西去。”经过一番采购,年轻员工发现,54人份的各种物资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心中有所疑虑。岑叔说:“本来这太阳就够毒了,大家抢修完回来休息时没有风扇、凉席怎么过?这个一天都不能等,这钱得花。”

广东电网珠海金湾供电局岑永源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伙食是后勤工作的重点。每当岑叔低头沉思,大家就知道他又在考虑下一顿的菜谱了。海南的热带气候和地方伙食让许多队员不太适应,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症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岑叔排除万难,用有限的物资搭建了炉灶,当起了“火头兵”。每一道菜,每一碗汤,成了大家充饥解暑的美味良药。
岑叔也有皱眉头的时候,“唉,今天饭菜剩得有点多,浪费啊,看来要继续改进。”满脸神情惋惜。跟购置物资时的豪爽判若两人。这样豪爽而又“小气”的岑叔,让人觉得既可敬,又可爱。(卢奕霖)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