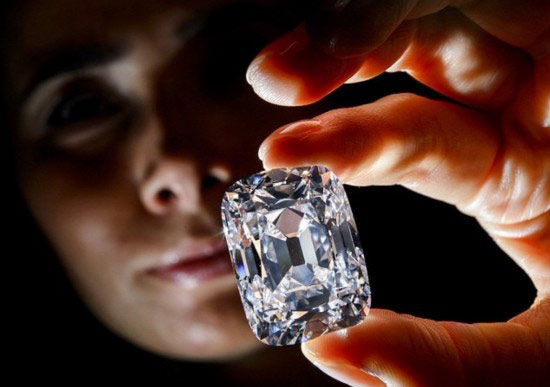本就不符合資格為何還抱怨?輪候時間本就長,門檻再放寬豈不更等不到房?2月21日本報刊登《保障房輪候期不敢結婚》一文后,受到頗多爭議。保障房應該如何管好這個老話題,又一次激起漣漪。
管好保障房並不簡單,在需求溝壑難平的現狀下,保障房系統的現狀顯而易見。一切糾結背后,還有個問題遲遲未解,該不該讓被保障者擁有產權,是保障房制度未來應該深思的問題。
購房后收入暴漲,保障房應有退出機制
張帆住進保障房,已經有近3年的時間了,按照他的說法,這是他人生大變樣的三年,“房子有了,車子也有了。”
“外人看來,我是撿了一個大便宜,但從保障房規則來看,我沒有任何違規之處。”張帆坦言,申請兩限房源於對保障房制度的“深刻”理解,原本居住在老城區平房的張帆,父母均是退休職工,退休金加起來不到5000元,從沒分過房,幾十年一直住在平房,還是公房,符合北京市保障房申請規定,“但把我算在其中,我家的收入就不符合標准了。”
研究保障房申請標准后,張帆讓父母以二人家庭為單位,申請了兩限房。
那時的兩限房還不是人見人愛的香餑餑,經歷幾次搖號后,張帆父母2008年底選中保障房,選房、裝修都是張帆一手操辦,“父母申請孩子住,孩子申請父母住,我身邊這樣的例子不少。”
如果故事僅止於此,還無法顯示保障房制度的另一種現實——2010年,張帆所居住的原住房拆遷,張帆用拆遷款再次購置房產,一年之內,張帆從一個無房戶,變成了“存折上有七位數存款”的人。
因為拆遷是在購買保障房之后,按照保障房制度,張帆一家並不屬於騙購范疇。事實上,因保障房制度以申請者自劃家庭范圍為單位,即便父母有數套房產,隻要成年子女本人符合申請標准,亦可申請兩限房。“我身邊就有這樣的例子,家裡房產就值八位數,孩子還等著搖號呢。”
不僅如此,對於購房后收入暴漲、資產變動等情況,保障房制度均未作任何規定。
“我們這個小區入住3年時間,小區車位已經滿了,路邊都停得差不多了。雖然豪車沒見幾輛,但十幾萬的車有的是。”從車位看住房人,張帆表示不能簡單說“權錢交易很多”,“但至少說明一點,住在裡面的人,有打擦邊球的。”
“鄰居裡有博士生,上學沒收入時候申請的”
“目前的保障房分配制度,很難百發百中,把房子分到需要的人手中。”研究保障房制度多年的律師衛愛民表示,分配效率一直是保障房建設的一大難題。
事實上,張帆的例子也不極端,從“開寶馬住經適房”成為保障房的時代印記開始,分配公平、退出機制等問題均成為公眾質疑對象。
一切的開端,要追溯到20世紀90年代。1998年7月3日,《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頒布並實施,這部終結住房實物分配、開創住房分配貨幣化的綱領性文件中,明確提出“對不同收入家庭實行不同的住房供應政策。最低收入家庭租賃由政府或單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購買經濟適用住房﹔其他收入高的家庭購買、租賃市場價商品住房。”通知中,將未來中國城鎮住房體系描述為“以經濟適用住房為主的住房供應體系”。
進入21世紀后,“市場價商品住房”成為主體,比市場價低很多的經濟適用房,反而成為住房供應體系中矛盾的一環,在經濟適用房內,人們既能看到低收入人群,也能看見開奔馳寶馬的“有錢人”。
2005年6月,新華社記者對著名經適房社區回龍觀進行探訪。報道披露,200平方米的“經適房”,房主裝修便花費30萬元,更有一套二手經適房出售資料中注明“230平方米、6台電視、7個空調”……
此后幾年,經適房開始淡出人們的視野,申請門檻更高、戶型面積限制更為嚴格的“限價房”成為保障房主流。
“在我的理解裡,經適房和兩限房沒有本質不同,只是操作手法有差異,實質就是給符合標准的人便宜買房子的權利,至於誰符合標准,就得各顯神通了。”張帆曾詢問自己小區的住戶,發現住戶有幾種構成——符合申請條件的京城老人或其子女,有北京戶口的年輕公務員、事業單位員工,因拆遷獲得安置資格的拆遷戶。“真困難的很少,何況收入很低的家庭,也拿不出幾十萬買房。我鄰居裡就有博士生,人家上學沒收入時候申請的,房子一天沒住過,直接租出去了,一個月能租4000元。”
“設立保障房制度是對最困難社會成員進行救助”
2009年,著名經濟學家茅於軾劍指經適房,表示“它既不講效率,更不講公平,比賭博還要壞……”激烈的言論旋即引發輿論熱議,茅於軾對於廉租房不應配衛生間的言論,更使得許多網友攻擊茅於軾“為富人說話”。
“直到這兩年,許多人才深刻理解到廉租房不配衛生間這話的道理。”2012年初,孫宇提交兩限房申請材料,身為老北京人,孫宇並不缺少房子,隻不過在父母名下的房子,並不妨礙他“申請個試試,碰上了就撿個便宜”。
“我們並不是騙購,我們只是在利用游戲規則。你可以查查,申請經適房、限價房的,遠比申請廉租房的人多,這說明什麼?說明很多人的心態不是著急找房住,而是等著抽大獎。”北京市住保辦網站的官方數據,印証了孫宇的感受,截至2013年2月25日,北京市經濟適用住房備案通過94325戶、限價商品住房備案通過180467戶、廉租住房備案通過28331戶,等產權房的,比等房住的多出10倍。
“從邏輯上講,設立住房保障制度的目的,是對最困難的、自身無法按照市場價格解決基本住房需求的社會成員進行救助。居民一旦能夠按照市場價格解決自己的基本住房需要,就不應再成為保障對象。”中國科學院大學管理學院董紀昌教授指出,如果將衣食住行均無憂的社會成員也納入保障范圍,則是將保障泛化為普遍的社會福利:“幫助社會成員擁有資產,不是國家保障制度的內容。”
有產權保障房的問題還在於,因為經適房、兩限房產權已歸於業主本人,並無實際“退出機制”存在,政府頂多在二次流通過程中收取一定費用,在此之后,原本就稀缺的保障房資源,將直接通過“經轉商”,流入商品房市場。
對此,著名經濟學家張曙光曾對媒體表示,保障性住房和商品房市場應該是兩個不同的市場,並沒有必要“存在一個未來將流向商品市場的半保障性質產品”。 (應採訪者要求,張帆、孫宇為化名)
未來
“十幾萬的申請者,
光消化現有需求
就得多少年”
“做大保障性住房存量是實現應保即保的前提條件,大力發展公共租賃住房,才能滿足這個條件。”買的解決不了問題,租的未必不能解決,武漢大學中國住房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曾國安建言,公共租賃住房才應該是保障房體系的核心。
“住房保障存在應保未保、不公平等問題,應該明確公共租賃住房是我國住房保障的發展方向,是未來城鎮住房保障體系的核心。”曾國安表示,經濟發達國家和地區住房保障的發展歷程,顯示了公租房在住房保障中的顯著作用,確保公租房建設、制訂合理准入、騰退機制,才能更好地發揮公租房的保障作用。
保障房體系也並非沒有改變,2011年初,北京市住建委明確提出“住房保障由‘以售為主’向‘租售並舉、以租為主’轉變”的目標,隻不過實施仍顯緩慢。
“從建設和運營的收入上看,公租房投資期長、收益低、運營成本高,僅靠政府投入很難滿足社會對保障房的巨大需要量,因此解決公租房建設資金來源問題,最終還要靠吸納全社會更多的民間資本參與到公租房的投資建設中來。但由於利潤相對低且分配和銷售等主動權在政府手中、參與機制不順暢等原因,目前民間資本直接參與保障性住房建設的積極性不高。”董紀昌表示,由於租賃性保障房“無利可圖”,成為建設最大障礙,要提高民間資本直接參與公租房建設的積極性,必然需要設法降低民間資本進入該領域所面臨的風險——包括宏觀經濟環境、資源環境、市場環境以及法律、政治環境等風險,保証民間資本能得到合理的投資回報。
與此同時,兩限房、經適房已積累數以十萬計的申請者,如何轉換也將成為難題。
“十幾萬的申請者,政府說取消限價房,大家的反對聲音得多大?可是不取消,光消化現有需求就得多少年?”2012年2月至今,限價商品住房備案通過申請者又增加3萬有余,高速擴張的需求,正在呼喚保障房體系改革的盡快出台。如孫宇般等待著的申請者,心情更為復雜:“如果全面轉為隻租不賣,也許申請人一下就少去很多,但誰有這個決心干這個事,我持懷疑態度。”主筆:吳楠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