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因為缺乏具體標准,寬帶消費者的利益無法真正得到保護﹔有線寬帶網絡接入難順暢﹔寬帶不寬、斷網頻繁、服務差嚴重影響了消費者的使用體驗﹔關於寬帶的投訴量大增。
根據中消協的統計數據,2012年全國消協組織受理互聯網服務投訴21037件,同比增長1.9%。其中,網絡接入服務投訴16708件,佔互聯網投訴的79.4%。
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這種現象,也使得監管破題乏力?通過調查,《中國經營報》將為您揭示一條不為人知的利益鏈條。
“10M帶寬,每月最低隻需支付66元!”看到塞在門縫裡的某寬帶運營商的廣告,家住北京市海澱區蘇州橋某社區的王大虎氣就不打一處來。
2011年4月,王大虎原本採用的寬帶服務到期,去續費時,工作人員熱情推薦他將原來的2M帶寬升級到4M。考慮到4M服務價格雖貴,但網速更快,而且如果能夠一下繳足兩年,月租費與2M費用差不多,王大虎爽快地認購了4M帶寬。
但隨后,王大虎就覺得上當了,家裡的網速不僅難以感覺到有所提升,斷網頻次反而增加了,晚上上網高峰期經常打不開網頁。
王大虎找到服務商投訴,因為工作和生活離不開網絡,包括查資料、炒股、網游娛樂等,他希望服務商給出賠償,但對方每次都以“斷網隻有持續超過24小時才可能有賠償”說法推脫。
王大虎最終沒有更換寬帶網絡接入服務商(ISP),一方面,他明白了“便宜沒好貨”,所謂低價的4M和相對更好的性價比,隻不過是ISP們促銷牟利的幌子﹔另一方面,因為小區物業收取了該運營商的“好處”,該小區隻允許有限的一兩家服務商提供接入服務,另外一家的口碑還沒有這家好。
知假售假
王大虎們的遭遇有個通俗形象的稱謂:假寬帶。
早在2011年12月,DCCI互聯網數據中心(下稱“DCCI”)發布的《中國寬帶用戶調查》顯示,2011年前三季度中國固網寬帶與3G用戶數累積達到1.5億與1.02億,但中國絕大部分互聯網用戶在使用“假寬帶”。
所謂“假寬帶”,DCCI給出的定義是網民使用的實際寬帶下載速率低於運營商提供的名義寬帶速率。DCCI針對辦理不同帶寬的固網寬帶用戶進行了上網平均速度調查,結果發現,超過半數用戶上網平均速度達不到標定速度。
具體而言,使用4M寬帶的用戶中,平均速度在400KB/s以下的佔91.2%﹔使用2M寬帶平均速度在200KB/s以下的佔83.5%﹔使用1M寬帶平均網速100KB/s以下的佔67.6%。
很顯然,費用越高、網速越快的ISP服務中,“假寬帶”反而佔比更高。
“國內假寬帶的情況非常普遍,原因也不一而足,但就其實質來說,‘假寬帶’就是‘路少車多’,每名用戶從ISP那裡獲得的實質帶寬無法達到名義購買價。”某電信設備制造公司高管李雲告訴《中國經營報》記者。
李雲創立的公司從事無線路由器研發制造。但與一般的無線路由器廠商不同,李雲專門針對國內網民帶寬有限、“假寬帶”現象普遍的現狀,在自己生產的無線路由器上提供多重加速功能,改善用戶體驗。
也因此,李雲對國內ISP“假寬帶”的潛規則“門兒清”。
“我們平常所稱的2M或4M帶寬,一般是指下載時的最高網速。雖然說某一用戶的網速究竟是多少,需要根據具體時段、具體位置進行測量才能准確無誤,但整體來說,北京市二三級運營商提供的4M帶寬,高峰期平均下載速度1M都不到,屬於正常現象。”李雲說,對於假寬帶,北京市的ISP們心知肚明,二三級運營商裡這種情況更為嚴重。
利益糾葛
因為深知二三級ISP的盈利模式,李雲家裡安裝了北京聯通的3M包月帶寬,每月120元。這一價格確實較王大虎每月平均不到80元的4M帶寬價格為高。
“3M帶寬的售價之所以高出4M,根本原因就在於兩者的盈利方式不同。北京聯通是寬帶光纖的直接鋪設者和寬帶服務的一級運營商,他們會將部分帶寬批發給二三級ISP,二三級ISP再將其加價零售給普通網民。”李雲說。
但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同等服務價高者不可能獲得用戶青睞,所以,二三級ISP要麼致力於一級ISP骨干網未曾到達的社區進行“最后一公裡”的神經末梢升值服務,要麼向小區物業購買獨家入戶權“壟斷”經營,要麼售賣“假寬帶”——更快的網速反而更低的市場售價。
國內的一級ISP主要包括電信、聯通等大運營商﹔而在北京,諸如歌華有線、長城寬帶、方正寬帶等都屬於二三級ISP。
不難發現,作為ISP零售的主力,二三級ISP盈利模式上天然有提供“假寬帶”服務的“囚徒困境”。
除此以外,網民購買的“假寬帶”服務,也可能是“黑寬帶”。
所謂“黑寬帶”,即某單位購得的帶寬,在完全有富余的情況下,主管帶寬的高層會將部分帶寬以合適價格私下轉賣給二三級ISP獲取個人私利。
“這種情況有一個很具體的特征,即用戶個人電腦顯示的IP地址(相當於互聯網服務中的身份証)與外面看該用戶的IP地址不一致。因為這樣做的二三級ISP甚至更小規模的運營商,必須通過內外網技術將前述非陽光獲得的帶寬進行‘洗白’,將本來並非自己的網絡帶寬偽裝成屬於該運營商的。”李雲說。
監管難題
不過,如果因此就將“假寬帶”責任全推給二三級ISP也不公平。畢竟,他們無權像電信、聯通一樣在國內架設寬帶骨干網,隻能從大ISP“虎口”中批發再零售“討生活”。也是看到這些問題,國家發改委2011年對中國電信和聯通等一級運營商發起了反壟斷調查。
2011年底,中國電信和聯通做出的整改承諾稱,將對骨干網的互聯互通進行擴容。在此基礎上,工信部2012年4月發起了覆蓋全國的“寬帶普及提速工程”動員部署大會。時任工信部部長苗圩明確提出2012年我國要實現4M及以上寬帶接入產品市場佔比超50%、新增光纖到戶覆蓋家庭超過3500萬戶的發展目標。
2013年初卻有報道稱,囿於光纖寬帶投資回報周期太長、投資回報率太低,國內寬帶運營商2013年將對實裝率低的地區減少或停止寬帶提速普及工程。
就此,工信部相關司局以及中國電信、中國聯通都向媒體澄清並無“反水”之說,寬帶普及提速工程也不會剎車。工信部和中國電信、聯通兩大“寡頭”提供的數據還顯示,2012年,兩者在寬帶方面的投資已經超過600億元﹔年內新增1.93萬個行政村通寬帶,行政村通寬帶比例從年初的84%提高到了87.9%﹔寬帶普及提速工程實現年度目標,使用4M及以上寬帶產品的用戶比例超過63%。但市場針對“假寬帶”及背后我國電信業的運行體制爭議卻未平息。
兩會期間,騰訊公司CEO馬化騰“一針見血”,他認為,信息高速公路應該理解為像公路、鐵路、機場、電網一樣的基礎設施。因此他呼吁,互聯網的基礎建設尤其是寬帶應該由國家來承建。而不要把這些交給運營商移動、電信、聯通來參與:這些運營商肯定要算一筆賬,設備貴、電力貴、帶寬貴、光纖鋪設也貴,他們會把這些成本都疊加在老百姓身上,所以造成國內工資水平比別人低,但上網資費卻比其他地方貴幾倍、十幾倍。
知名電信專家項立剛也曾公開表示,中國大規模的光纖寬帶網路建設,僅靠運營商不現實,國家要投更多的錢。
而在移動、電信和聯通三大ISP看來,幾十年來,電信基礎設施確實是由國家來建,但國家也肯定要有具體的承建主體,最終還是三大ISP而不可能交給社會企業。
或許,正是如此環環相扣的利益鏈,導致“假寬帶”最終破題乏力。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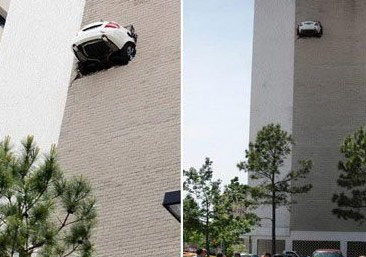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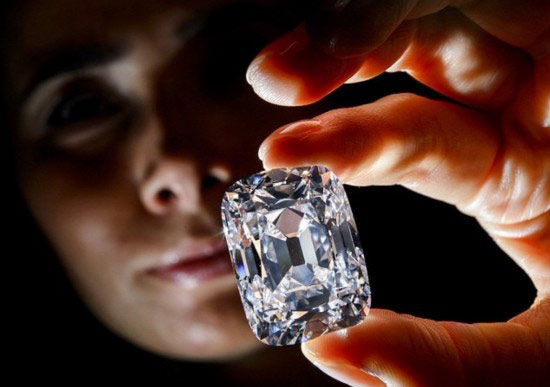

















 公交車半路載客致兩死
公交車半路載客致兩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