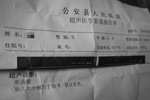锦屏电站早期建设者风餐露宿的艰苦生活条件

人背肩扛运输物资

水电站建设前期的肩挑背扛
“锦屏究竟是个什么地方啊?”坐在颠簸的车上,这个疑问也随着咱几个的脑袋摆过来、甩过去。昏昏沉沉睡一觉醒来,没有到;迷迷糊糊再睡一觉醒来,还没有到……
车从清晨一直开到夜晚,终于在一个有些灯火的地方停了。曾新华告诉我们:“这里叫二区,离工地还有几十公里路。现在是雨季,路不好走,等我明天先去探探路再回来接你们。”我不理解他所说的“路不好走”的真正涵义,但当我看到这里的山时我想这后面的路绝对比这一整天的盘山道路痛苦得多。在这里我才发现汉字的“山”造得胖了些,或者说压根儿就不是比着锦屏山造的。锦屏山的山,瘦高陡峻,挤兑得雅砻江哪还有峡谷的样啊,那叫一个蹩屈,蹩屈的成了一条山缝。坡陡崖险,唯有岩羊攀壁;林密草盛,只闻蛇嘶猿啼。“在锦屏,30度的坡就是平地。”难怪两院院士潘家铮先生当年形容锦屏是“峰如斧劈江边立,路似绳盘洞里行”。
一位新华社记者风趣地讲:“苦、险、难是锦屏工程款待二滩人的三道大餐”,此言一点也不虚。锦屏水电工程不仅以具有305米的世界最高拱坝和具有120公里的世界最大规模的引水隧洞而汇聚了诸多的世界级难题,而且以施工条件异常艰苦而闻名。感动中国人物四川凉山木里县马班邮路乡邮员王顺友送信的地方就是锦屏工地的倮波乡。一位采访王顺友的记者,当时从县城出来骑着马,觉得非常刺激、新鲜,当到了雅砻江边时,吓得根本不敢骑马,腿都发软,抬头是悬崖峭壁,低头是波涛汹涌的雅砻江。新华社张严平在他那篇获得全国新闻最高奖的文章《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中讲,“整整一天,我们一直跟着王顺友在大山中被骡马踩出的一趟脚窝窝里艰难地走着,险峻处,错过一个马蹄之外,便是万丈悬崖”。同样,在锦屏工程前期,交通靠走、通讯靠吼、照明靠油、治安靠狗,住的就更别提了,用他们的话就那就是“天当被,地当床,抱着石头当新娘”。“第一批人是爬进锦屏的,第二批人是走进锦屏的,第三批人是坐车进锦屏”,就是对前期行路难的真实表述。锦屏前期住悬空的铁皮房,喝山涧中的“矿泉水”,整月吃方便面和咸菜,晚上睡觉要带上口罩的难忘画面至今还时常浮现在二滩人的眼前。“山间铃响马帮来”、“滚石也砸CEO”、“不是军人也拉练”、“腰缠万贯没饭吃”、“电话通了,女朋友也吹了”等一个个经典的故事也在锦屏经久相传。
锦屏条件再苦、环境再险,可二滩人从不叫苦,也毫不畏难,因为他们明白:选择了水电,就意味着选择了吃苦;选择了水电,就昭示着选择了奉献与奋斗。
要说锦屏的“苦、险”是有时段的,可锦屏的“难”却始终贯穿于工程建设全过程。如果没有二滩人不怕挫折、不怕失败、坚韧不拔、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一个个震撼世人的奇迹就不可能创造。
单说锦屏二级水电站要建设7条隧洞,总长近120公里,最大埋深2500米,是世界上埋深最深、综合规模最大的水工隧洞群。由于大埋深产生高地应力,开挖时会产生“极强岩爆”,它被国内外专家称为地下工程施工中没有任何征兆的“癌症”。同岩爆一样,锦屏工程的高压突涌水,也被国内外专家认为没有根治的特效“药”的世界级难题。
毫不夸张地讲,在进入岩爆施工段,每一次进洞都面临着可能出不来的危险,如果没有坚韧不拔的决心和忘我的境界,给多少钱谁都不愿再进洞。一次,一家媒体的电视记者到锦屏采访,恰遇引水隧洞刚发生岩爆,他们提出去拍摄,当二滩员工给他戴上钢盔、穿上防弹背心,记者手就开始发抖,当时就讲:“现在我感觉到啥叫战场,‘光荣’的感觉是何等恐惧”。
治理高压突涌水过程中,二滩人与参建各方人员,包括国内外著名的治理突涌水专家、院士,也经过很多挫折和失败。那些日子特别漫长,二滩公司的领导、工程技术人员、项目负责人天天穿着雨衣在隧道进进出出,当时二滩公司学地质的胡兵博士在洞子时间待的过长,出来时腿都一瘸一拐;当时负责锦屏工程现场工作的公司领导也曾连急带累地晕到在工地。但二滩人与各方参建者硬是靠着坚韧不拔的决心,从失败中找到良策,使无药可救的突涌水顽症终于有了根治的灵丹妙药。
 |  |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