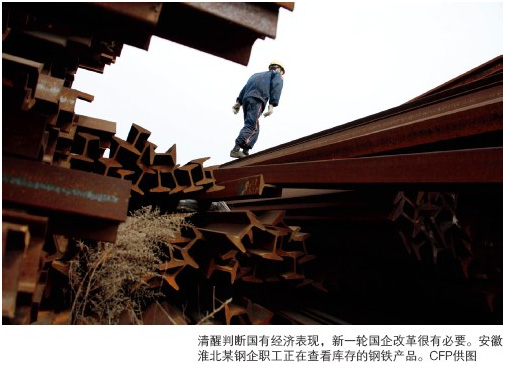国有企业改革在很长时期里被视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但是,过去几年里国有企业改革似乎沉寂下来,一些行业甚至出现了所谓“国退民进”的现象。同时,从2003年以来国有部门的经营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许多人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到位,再谈国有企业改革似乎是多此一举。我认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在当前形势下,很有必要启动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
清醒判断国有经济的表现
国有经济的表现到底怎么样?我们对此应该有一个清醒正确的判断,这是制订国有经济改革政策的前提。现在有些机构或者学者的判断就是,国有企业效益搞得好,为什么要改呢?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改革的必要性不大,至少改革的紧迫性不强,因为根据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实用主义改革逻辑,没有必要出于一种教条而改革,更无必要为了改革而改革。但我却有截然不同的判断:国有企业与十年前相比的确更好,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上世纪末的改革红利和本世纪前几年的重化工业景气带来的;而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总体而言差距很大,而且越来越大。
国际上最通用的指标有两个,一个是采用净资产回报率(ROE)指标来衡量效益。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年报的数据来算,国有企业净资产回报率明显地低于私营企业,也低于外资企业。如果以税前实现利润来计算,2003年的时候国企和私企的这个指标还差不多,私企13%,国企12%,2007年国有企业净资产回报率略微高于15%;民营企业已经是23%了,非常平稳地上升,2009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稍微有点下跌,但已经越来越多地领先于国有企业。还有一个是采用全要素生产率(TFP)指标来衡量效率。几乎所有经得起推敲、具有引用价值的的研究都显示,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远远低于私营企业。一项研究表明,过去30年国有企业TFP年均增长大概1.5%,而私营企业是4.5%。无论是ROE指标,还是TFP指标,在过去十年国有企业发展壮大最快最明显的时期,都远远低于私营企业。尽管过去十年是国有企业盈利增长最快的时期,但实际上盈利集中在少数具有所谓“市场力量”的企业,11.5万家国有企业目前的亏损数达到30%以上。而民营企业的亏损10%多一点,10%亏损率在市场经济当中是正常的。
当然,有些学者也会强调国企效率较低是因为国企承担了很多社会责任。但现在所能得到的所有分析都是零碎的、不具备引用价值的。我个人承认这方面的因素,但这个因素并不足以推翻上述判断。
国有企业即使跟十年前的面貌相比有很大改观,也是因为上个世纪末对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改制重组,这些年来一直在享受改革红利。而上一轮改革的边际效果逐年递减,如果仅仅坐享其成,以前的改革红利将消耗殆尽。因为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上世纪末改革之后几年,国有企业ROE大幅度地提高,而2007年之后它基本上是停滞不前,甚至有下降趋势。当然,国有企业2003年以来的快速发展壮大,也与这一轮重化工业景气有很大关系,因为保留下来的国有企业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重化工业领域的大企业。但问题在于,重化工业的鼎盛时期也会过去,重化景气带来的红利也会消失。
国有企业过去几年在技术创新、技术进步方面的成绩也成了许多人争辩国有企业优越性和竞争力的证据。但我们的研究结论恰恰相反,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也是明显比民营企业低很多。这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投入的创新资源取得了多少创新成果就可以比较出来。国有企业在过去几年投入了大量的研发经费,也取得了成果,但是我们可以进行一下比较,比如说,国有企业每投入一亿元研发支出所获得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大概是18,而民营企业43,差距不只一倍;国有企业每100名研发人员获得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是3.7,民营企业是7.4,差距也不只一倍。可以看出,民营企业的创新效率比国有企业高一倍以上,这个是中国科技统计研究的官方数据。
国有部门作为一个整体而言,从ROE、TFP、创新效率等典型指标来看,其总体效率明显不如民营部门。但是许多经得起推敲的严肃研究都发现,国有部门占用了与其规模和效率不相称的经济资源和创新资源,而且很多时候是以相对较低廉的价格占用了重要资源,并且国有企业天然的“政商联结”加重了这种情形。想一想,效率低的部门反而能以相对低廉价格获得更多资源,这是什么情形难道不是很清楚吗?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国有部门存在大量的经济租,严重扭曲了资源配置机制,对效率高的民营部门获得资源形成了“挤出效应”。另一方面,国有部门的经济租和营业利润与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基本没有,老百姓没有享有应有利益。国有部门大约雇佣了三四千万员工,员工当然得到了工资收益,但这些人只不过占我们全部人口的3%、全部从业人员的5%、全部城镇就业人员的10%,所以并没有惠及多数人。从这个角度而言,现在的国有经济不是“全民所有”,而是“全民没有”。从上面这些分析来看,国有企业到底要不要改不是很清晰吗?
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方向
中国过去30多年平均每年9.9%的高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靠投资拉动,意味着要不断投入经济资源,投入大量的要素来发展经济。这是一种典型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如果通过国企改革,让效率高的民营部门获得更多的资源,而缩减效率低的国有部门规模,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资源配置的扭曲状态,完全不需要这么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就可以保持相对比较高的增速,这非常有利于一直讲
的转变发展方式。依靠这么多的投资和大量的资源消耗、资源投入来维持高经济增长,发展是根本没法持续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发展方式转变进展不大,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因为国有企业处于粗放、低效率的发展状态。而且我们也做了一些分析和测算,现在整个国家国民经济的资源配置当中,国有部门的强势以及同政府存在天然的千丝万缕的纽带关系,使它更容易获得资源和各种商业机会,政府隐含的担保和救济也使它们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获得较多资源,使资源配置扭曲、竞争无法平等。而民营企业为了抢夺经济资源,可能会采取更加不理性、不光彩乃至不合法的方式,这样整个经济就会出现“政商联接”大竞赛和资源争抢大竞赛,而不是效率提升大竞赛和自主创新大竞赛,最后的结果是,高增长伴生着严重的过度投资和信贷膨胀以及金融隐患,公司治理和宏观审慎出现严重问题,收入分配扭曲和财富掠夺成为常态,而高增长也将戛然而止。看一看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东南亚国家的历史状况吧,就是这样的情况。
 |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