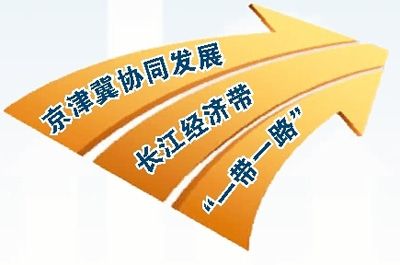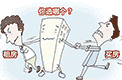“專車第一案”庭審避開了私家車作為專車載人的合法性問題,但不管其結果如何,這問題都該提到法治破題的層面。
濟南滴滴專車司機陳超被認定開黑車罰款2萬后,因不服起訴客運管理中心。昨日,這起被稱為“專車第一案”的案件在濟南法院開庭審理,其中被告的行政主體資格和行政權限成為雙方爭議焦點。
專車是非之爭由來已久,上升到訴訟層面的尚此一例,盡管此案是專車處罰行政訴訟之個案,但這極有可能成為專車之爭的分水嶺,也是互聯網+產業模式迎接挑戰的一塊試金石。也正因如此,它廣受關注。
拿該案來說,庭審現場雙方爭鋒的焦點,是涉事客運管理中心的行政處罰資格,而非私家車作為專車載人的合法性問題。本質上,它並未挑戰現有的法律定義框架。而誰是誰非,終究還得看最終判決“蓋棺論定”。
有專家分析,私家車從事客運服務不論是巡游攬客還是預約用車性質,均被現有法律明令禁止,在此情境下,期待涉事法院主動表態支持“專車第一案”中的私家車營運行為不現實。但公眾心系此案,不只是希望在法律裁決個案上的定訟止爭,更是希望它能為專車合法性困境破題,避免它繼續游走在灰色生存的狀態。
得看到,專車服務是典型的互聯網+創新性產業模式,客戶、支付模式、路線選擇、平台管理等都源於移動互聯網。而其合法性之爭則是互聯網創新跟既有的監管方式沖撞的產物。盡管說,專車不僅解決了客運市場的剛性需求,還對減緩城市交通壓力、利用閑置車輛等方面產生積極意義。但它帶給傳統出租車行業以巨大沖擊,專車興起還引發的哥們對“份子錢”過高質疑。
處在這新舊模式碰撞的節點,公共管理部門的態度也頗具導向意義。它如果因循不完善的法規,可能會找出一萬條反對專車發展的理由﹔但政府和司法更需要考慮的是,固守現有的法律考量視野會否扼殺創新,錯過互聯網+帶給整個中國彎道超車的機會。去年11月23日,交通運輸部針對移動互聯網預約車問題答記者問時,提出了“以人為本、鼓勵創新、趨利避害、規范管理”的十六字方針,將“鼓勵創新”放在了重要位置,就頗具意味。
實質上,專車在北美也是一種新事物,著名的Uber公司也曾面臨政府禁令、釣魚執法、出租車行業抵制等情形。它之所以能夠在“逆境中”茁壯成長,不在於創辦者鍥而不舍的精神和雄厚的民眾基礎,而在於法律、政府等願意趨從互聯網大勢。盡管洛杉磯市交通部門也曾對Uber發出“勒令停止通知函”,但其政策壁壘漸次消除,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就對Uber等提供的租車服務表示支持,認為嘗試扼殺租車應用,將會阻礙競爭。
因此,不管“專車第一案”判決結果如何,專車合法性問題都該提到法治破題的層面。畢竟,當下正是李克強總理提到的“風口”,政府作為與司法的方向都應順應這個“風口”,而不是糾纏於那些刻板而過時的法律條文。也唯有法律與時俱進,再碰到類似糾紛時才不會出現專車是非判斷上的分野。
□朱巍(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