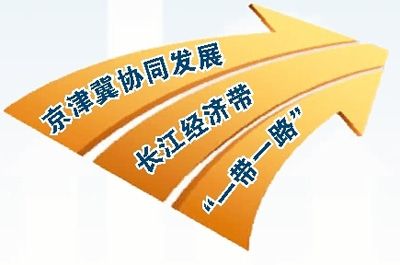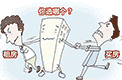桐廬,這個地處浙西北山區的小城山清水秀,有著中國最美縣城之稱。桐廬不僅因為自然美景出名,人們一進入桐廬縣界就能看見一塊大石碑,寫著“中國民營快遞之鄉”。
我國是世界第一快遞大國,2014年快遞業務量達140億件,其中100億件來自“三通一達”四家快遞企業:申通、圓通、中通、韻達。而“三通一達”的老總,都是浙江桐廬人。
為什麼桐廬能成為中國民營快遞的發源地?這個小城蘊藏著怎樣的奧秘?新華社記者和“三通一達”負責人相約來到他們的家鄉。
先吃螃蟹的人:“20多年的變化天翻地覆”
記者從桐廬縣城出發,向西走驅車一個多小時抵達鐘山鄉,一路綠色環繞,山路蜿蜒狹窄。“三通一達”幾位老總的家鄉都聚集在此。
鐘山鄉夏塘村村民詹雲榮告訴記者,由於山地多農田少,守在家裡隻能勉強混飽肚子,想致富隻能走出大山。
“讀小學五年級時,我代表鄉裡參加全縣數學應用題比賽,那是第一次走出大山、第一次到縣城。”中通快遞總裁賴梅鬆的老家在鐘山鄉最偏僻的天井嶺村。想起當年,45歲的賴梅鬆感慨萬千。
1993年,聶騰飛、聶騰雲兄弟離開家鄉桐廬縣鐘山鄉夏塘村,到杭州打工。當時,杭州集中了一批外貿企業,隔天就要往上海送外貿報關單,發中國郵政需要3天時間,企業自己跑成本又太高。兄弟倆敏銳地捕捉到了商機,替人出差跑腿送件。剛開始,送一單的價格是100元,除去來回的火車票30元,每單可以賺70元。一年下來,兄弟倆賺了2萬元,獲得了“第一桶金”。
之后由於業務擴大,聶騰飛的大舅子陳德軍也加入進來。幾個年輕人騎著自行車穿梭在杭州、上海等地的大街小巷,翻破了無數張地圖,吃盡了苦頭。
1998年,陳德軍接手掌管申通快遞。1999年,聶騰雲再次創業,創辦韻達快遞。2000年,喻渭蛟用借來的5萬元創辦了圓通快遞,租的是150平方米的倉庫,全部設備就是兩輛自行車和兩部電話。2002年,賴梅鬆從木材生意轉行,瞄准了快遞業,創辦了中通快遞。
快遞桐廬幫留給外界的印象頗為神秘,有傳言說這四家企業的老總彼此互有交集,韻達快遞常務副總裁周柏根說:“一開始申通、圓通、中通的老板互相並不認識,但先吃螃蟹的人確實產生了影響和帶動作用。”
周柏根表示,“三通一達”的老總們有相似之處,一是非常能吃苦,因為那時桐廬的山村太窮了。二是做生意不隻看眼前利益。“今天錢進了口袋,還沒捂熱,明天又投資出去了。”
鐘山鄉黨委副書記李芸說,鐘山鄉全鄉2.2萬人、6700多戶人家。在桐廬快遞人艱苦奮斗精神的傳幫帶下,有一半人外出從事快遞業。
在鐘山鄉歌舞村,一名在外做了20多年快遞的村民感慨:“村頭巷尾,盡是歐式洋樓,20多年的變化天翻地覆。”
據桐廬縣商務局統計,全國由桐廬籍民營企業家創辦和管理的快遞企業已達2500余家,從業人員超過20萬,年營業額300多億元,佔據全國快遞行業將近60%的市場份額。2010年,中國快遞協會授予桐廬縣“中國民營快遞之鄉”稱號。
從“黑快遞”到“黑馬”:“我們的成就感很強”
從“黑快遞”到中國經濟的一匹“黑馬”,從夾縫中求生存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三通一達”在崛起之前曾經歷過風暴的洗禮。
我國舊版郵政法規定郵政業務專營,但對各企業間的商務件沒有明確范圍。早年的“三通一達”以及順豐,都以商務件作為主營業務,在夾縫中求生存。
“印象最深刻的是,這個行當是黑快遞,到處被打壓。”賴梅鬆回憶,當時沒有確立民營快遞的合法地位,快遞企業和郵政企業之間由於業務競爭,經常發生沖突。
“閣樓上藏著商務信函,自己的車輛被扣,隻能坐出租車送件。最怕的是快件被扣,沒法跟客戶交代。”一位在快遞業摸爬滾打十幾年的快遞企業大區經理告訴記者,那種感覺就像鏢局搶鏢。
2009年,修訂后的郵政法開始實施,民營快遞的合法地位確立。“黑快遞”企業也成為郵政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民營快遞企業有了開天辟地的意義。
圓通速遞副總裁郎鴻飛說:“從‘地下’干到合法,我們的成就感很強。現在政府對我們很重視,很多地方把快遞產業發展納入了當地規劃。”
“三通一達”四家企業的注冊地都在上海市青浦區,2014年納稅5億多元,成為青浦區的納稅大戶。
當記者問,創業時最激動的是什麼?周柏根說:“業務量沖破1萬票。因為是從零做起來的。之后從200萬不斷地沖到300萬、1800萬。”
加盟模式“分田到戶”:“打造中國的聯邦快遞”
“‘雙11’快遞洪峰來臨,為什麼能順利通過?”賴梅鬆認為,這得益於加盟模式,人手不夠可以叫親戚朋友。“三通一達”都是通過加盟模式創業,迅速在全國鋪設網點。
起初,“三通一達”的加盟制就是鼓勵員工到其他地區拓展業務網絡,包干到戶,按文件、包裹的不同價格繳納承包費,加盟商共用一個品牌,各自收取收件費,彼此之間實行派送費互免。
賴梅鬆又對加盟制進行了改良。兄弟分灶吃飯,獨立法人經營主體切割得很清楚,主要的轉運體系都歸總部統一調配。但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快遞網絡越廣,創業主體伙伴越多,蛋糕做好了大家分享。
賴梅鬆說:“‘三通一達’快遞企業實行的加盟制,就類似分田到戶,這也算是快遞行業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
“快遞人最自豪的是什麼?走遍全國,一分錢不帶都能解決吃住問題,因為到處都有網點,都是自己的同事。”申通快遞總裁助理陳賢紅說。
“有人說快遞業創造了就業崗位。實際上很多人起初正是因為找不到工作才干起快遞。”賴梅鬆說,中通快遞去年增加就業崗位6萬個,今年創造就業崗位10萬個。按照現在的情形推算,到2020年,中通的平台將超過100萬人。
“快遞公司的網絡布局就好比木桶原理,有一塊短板都不是好的網絡。”郎鴻飛說。然而,加盟模式的缺點也恰恰容易出現短板。由於企業總部對加盟商難以掌控,從而造成服務質量、安全標准難以統一。統計顯示,50%以上的客戶投訴出自加盟網點。
目前,“三通一達”逐漸將重要的轉運中心、省會級城市網點從加盟改為直營。相似度極高的發展模式,產生了不容回避的問題:四家企業之間同質化競爭嚴重。
“三通一達”普遍對電商件高度依賴,因而形成了高度同質化的市場。當前,中國快遞市場洗牌態勢加速,“三通一達”彼此之間的關系也有微妙變化,開始從競爭走向競合。2013年,“三通一達”加上順豐共5家企業成立了蜂網公司,每家各佔20%股份,在企業集中採購、可以共享的資源上展開合作。
“中國民營快遞要走向世界,應該抱團取暖,要有志於打造中國的FEDEX(美國聯邦快遞)。”郎鴻飛說。(記者崔俐莎、趙文君、方益波 郭宇靖、葉鋒)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