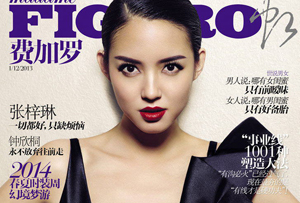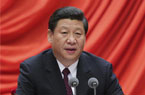李正秀在新加坡開辦的南蠻藝苑。

南蠻藝苑畫廊一角。

黃女士曾經經營的咖啡館放盤2年才成功出售。
編者按——
數據顯示,過去20年間,進入新加坡的中國“移民潮”加速,移民總人數約50萬~60萬,約佔新加坡總人口的10%~12%。2006年前往新加坡的李正秀先在新加坡工作,其后又投資畫廊,獲得了公民身份。但李正秀感到,近兩年移民新加坡沒那麼容易了,投資移民也很難再獲批公民身份。
對此,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陳企業解釋,隨著新加坡政府調整社會發展戰略並同時調整人口規劃,新加坡政府正對來自中國方面的移民,包括技術移民、投資移民,全面收緊名額。
而在澳大利亞,早幾年盛行的“買店鋪移民”政策(163政策移民)也有所修改,對主申請人留澳時間作出規定,“老公回國做生意,老婆‘坐監’(意指‘移民監’,比喻移民要像坐監獄一樣不能長期離開要移民的國家)帶孩子”的模式對普通投資移民來說難再復制。
文/圖 本報特派澳大利亞、新加坡記者 溫俊華
最新動態
澳大利亞商業
移民政策調整
2012年,澳大利亞移民局宣布調整商業移民整體框架后, 將原來的13類商業移民項目合並為3大類: 132簽証,188簽証和888簽証, 同時引入邀請制和技術甄選系統,打分因素更加細化和量化,並對個人資產要求及企業年營業額等方面的要求會有相當程度上的提高,而英語水平、教育程度、新技術開發等方面因素的考量也讓那些受教育程度高的中青年企業家得到優先申請的待遇。
2012年11月,澳大利亞政府再宣布實施“188C500萬澳元重要投資者移民”項目,隻需達到500萬澳元的投資要求,而對申請人的年齡、背景、語言、學歷並無限制。
經過一系列調整以后,澳大利亞商業移民政策已瞄准企業家精英和超高淨值人士。
澳大利亞132商業天才類移民簽証申請條件——
1. 主申請人55歲以下
2. 家庭淨資產150萬澳元以上
3. 持股30%以上,商業淨資產不少於40萬澳元
4. 申請前2個財政年度,企業年營業額均在300萬澳元以上
5. 投資規模不小於150萬澳元
投資策略
1 畫廊老板李正秀:“投資要走本地化”
2006年,李正秀第一次踏上了新加坡的領土,先通過旅游簽証逗留觀察了一段時間,后來通過朋友介紹在新加坡找到一份正式工作,辦理了工作簽証,決定嘗試在新加坡留下發展。李正秀或許並不知道,自己是踏著中國向新加坡移民的高潮出去的——過去20年間,進入新加坡的中國“移民潮”加速,移民總人數約50萬~60萬,約佔新加坡總人口的10%~12%。當然,其時的李正秀並不關心這些數據,她面臨的問題是自己在新加坡的路該怎麼走。
投資畫廊 水土不服
李正秀在國內從事與藝術品相關的工作已經10年,丈夫本身也是畫家,在昆明開設自己的茶室和畫廊。剛落腳新加坡的頭兩年,李正秀的工作也與老本行有關。兩年下來,在對當地市場也有所了解后,出於對藝術的興趣和淵源,加上朋友的鼓勵,李正秀萌生出自己投資辦畫廊的念頭。
但畫廊看似風光,經營起來其中的艱難隻有內行人明白。“我們行內有句話,想讓誰破產,就讓他去開畫廊。”李正秀笑說,但她就是喜歡藝術,認准了這一行。她還有一個初衷,就是通過自己開辦的畫廊,把自己在雲南認識的一些有才華的年輕畫家推介到新加坡市場。
通過半年的選址,李正秀最后把自己的畫廊“南蠻藝苑”落戶東陵購物中心,這裡是新加坡傳統的藝術和手工藝品商場,來自中國的古玩、字畫、陶瓷,來自中東、印度、東南亞各國的各類藝術品一應俱全。並且,商場坐落在新加坡熱鬧的商業街烏節路邊上,高端客戶比較多。
2010年,南蠻藝苑開張,李正秀按照自己的設想推出了多位雲南畫家的作品展,雖然畫作的藝術水平高,但由於畫家在國外知名度不夠,加上本地受眾也有一定的審美慣性,畫展的市場反應不如預期。艱難創業之際,正好也是兒子從昆明前來新加坡讀小學之時,李正秀一邊忙著聯系畫展一邊帶孩子,找學校,幫助孩子適應,還要牽挂著先生和昆明的生意,經常兩頭跑。
實施本地化 生意才起色
在經歷幾次不太成功的畫展之后,李正秀不再堅守己見,要在本地立足,就要迎合本地的市場——本地畫家和東南亞一些名家的作品帶有濃濃的南洋風情,容易贏得本地買家的青睞,那麼就從本地畫家做起。李正秀咬牙投入了20萬新幣,接連策劃了幾輪本土畫家和東南亞畫家的畫展,終於贏得了本地藝術市場和買家的關注。
畫廊打出名聲之后,李正秀偶爾再為一些優秀的中國畫家做推廣,漸漸地,本地買家也開始關注中國畫家,畫廊的展覽和生意贏得了良性循環,李正秀也開始忙碌起來,把自己的畫展拓展到了馬來西亞等周邊東南亞國家。記者造訪時畫廊正在舉辦“邱昌仁水彩個展”,這是李正秀憑借在馬來西亞拓展的關系贏來的。邱昌仁先生是馬來西亞著名水彩畫家,不少觀眾和買家慕名而來。
忙碌之余,兒子的懂事也很讓李正秀欣慰,兒子在自己身邊一年多后,就轉到老師家寄宿,每逢周末才回家,無論是讀書還是與同學朋友交往,都沒怎麼讓她操心。只是每逢在家,12歲的兒子總要黏著她,作為平時少陪伴的補償。
回過頭來看自己的投資之路,李正秀感觸最深的是“一定要跟上本地的步伐”。“新加坡政府對中小企業有很多幫助,隻要符合幫扶條件,政府在貸款、稅收等方面有不少優惠。而且,政府所有的規定都十分公開透明。”李正秀說,再結合對本地市場和文化的研究和適應,才有可能在本地立足。
專家訪談
2
培育自己的中產階級
新加坡調整移民政策
近兩年,從與周圍朋友的聊天當中,李正秀感到,“除非一些特別優秀的人才”,中國人移民新加坡似乎沒那麼容易了,新加坡公民身份也更難取得。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陳企業這裡,李正秀模糊的個人感覺細化成了具體的政府的人口規劃和發展戰略。
據陳教授介紹,為了配合新加坡新一輪社會發展目標,培育本國的中產階級,政府對來自中國移民的政策將有所收緊。
人物簡介:
陳企業博士,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競爭力研究所所長,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
廣州日報:因應經濟和社會發展,新加坡未來20年的總人口規劃是多少?依據是什麼?對移民政策有何指導?
陳企業:新加坡《人口白皮書》提出,到2030年,新加坡人口要達到690萬(目前),但這不是人口增長目標,而是因應新加坡未來經濟社會發展提出的人口需求目標。過去10年,新加坡制造業比例下降到29%,服務業比例增長至69%,服務業的人手是不可替代的,這意味需要更多人﹔其次,新加坡人口老化,需要人口增長﹔再次,政府希望20年以后新加坡人在經理、執行人員、專業人士等中的比例達到2/3,中產階級壯大意味著女佣需求的增長﹔另外,新加坡基礎設施建設也需要更多外勞﹔最后,基於防務需求,政府需要一些更年輕的移民,那些可以交稅、對房地產有支撐、對國家收入有幫助的人群。
因應上述需求,新加坡主要需要四方面的移民:建筑工人等勞動力﹔專業人士﹔女佣﹔一些有才干、支撐面廣、生產力高的年輕人。
廣州日報:針對中國方面的移民政策是否會有調整和變化,分別會對各階層,如技術勞工、高學歷人才和投資移民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陳企業:經過多年實踐,政府發現,與來自印度、印尼、馬來西亞這些國家的藍領移民相比,來自中國的藍領工人在融入新加坡本地社會方面的能力相對較差,主要表現在語言能力和飲食習慣上。由此,政府在移民政策上作出的調整是:企業需要聘請11個新加坡人,才允許聘請1個中國人,相比之下,企業隻要聘請1個新加坡人,就可以聘請2個馬來西亞人。
白領階層中的中國移民比較能融入新加坡社會,他們受教育程度高,素質高,但這一部分人近年來增長也不多,因為他們的第一選擇還是歐美發達國家。
而雖然現在投資移民比較多,但在投資移民多了以后,政府對他們的背景也開始比較謹慎,對非法人士也有遣送回國的案例。最后,相對來說,多數投資移民的目的地也是歐美和澳大利亞。
3 澳大利亞咖啡店、超市愈發艱難
2007年后,澳大利亞中國移民,特別是投資移民大量增多。這批投資移民一般從當地人手中買下咖啡店、小型超市等店鋪經營,在滿足兩年盈利的經營指標,拿到身份后把店鋪賣掉。
移民新政
為了從眾多的投資移民申請人中挑選出最優秀的投資者,澳大利亞政府於2012年推出投資移民新政,採取打分制,根據申請人的年齡、英語程度、經商經驗、公司淨資產、技術貢獻/專利等一些特定的因素進行評分,申請人必須先符合基本要求,且打分超過移民局規定的通過分數線才能得到批准。
在澳大利亞留學生陳誠的印象中,2004年他剛到阿德萊德的時候,除了留學生,周圍的華人少到“幾乎沒有”。“2007年后,中國移民,特別是投資移民大量增多。”陳誠說。
以陳誠所見所聞,這批投資移民一般從當地人手中買下咖啡店、小型超市等店鋪經營,在滿足兩年盈利的經營指標,拿到身份后把店鋪賣掉。“反正是掏錢買身份,很多人並不在乎店鋪是否真正盈利,賬面上做漂亮就可以。”陳誠說。
黃女士正是陳誠口中那批“投資移民”,4年前從廣州番禺移民到了墨爾本。一家人花了20多萬人民幣,通過中介辦好移民手續,在BOXHILL華人社區的一個購物中心花20多萬澳元買下了一家咖啡店,遵循著當時“老公回國做生意,老婆‘坐監’(意指‘移民監’,比喻移民要像坐監獄一樣不能長期離開要移民的國家)帶孩子”的一般投資移民模式,黃女士和讀初二的兒子開始了移民生活。
畢業於中山大學,在國內是公務員,好強的黃女士並沒有像多數移民太太一樣,聘請職業經理管理咖啡店,而是認認真真地做起了“老板娘”:請了3~4個兼職工人,自己每天早上7時准時開店,打雜,收銀,忙上忙下,一直到晚上7時下班。
由於華人社區飲食行業競爭很大,黃女士不得不盡量壓低產品的售價——其他社區的咖啡店,一杯咖啡能賣4.8澳元,黃女士這裡隻售3.3澳元。雖然成本壓力大,但在黃女士的盡心經營下,兩年間咖啡店還是勉強盈利,達到了政府對該類別投資移民的經營要求,黃女士一家也順利地拿到了永久居民身份。
之后,黃女士也沒有跳出拿身份后賣鋪的“俗套”,由於經營店鋪太辛苦,請職業經理支出又太高,黃女士權衡之下還是把出售信息交到了房產中介。但店鋪的出售卻不如想象中順利,前后兩年,談了至少3個買家,被拖得心力交瘁的黃女士一再降價,最后才將店鋪售出,售價與她自己最初的買價,最多“打個和”。
不管如何,在澳大利亞原有的投資移民政策下,黃女士總算達到了“全家移民”的目標,比黃女士再晚幾年的投資移民,要達到政策的要求就更不容易了——從2009年開始,澳大利亞移民局發現大多數商業投資移民到達澳大利亞后只是經營飯店、超市以及禮品店等小生意,對澳大利亞的經濟發展並無較大的貢獻,於是開始對現有的投資移民政策進行檢討,在2010年4月提高了部分投資移民類別的要求,但申請人數依然維持火爆。
移民之惑
融入才是大考驗
陳先生就是在新政下到來的。大半年前,陳先生將自己在上海的產業出售,舉家移民澳大利亞,落腳距離墨爾本市中心30公裡的BAYSWATER社區,開了一家大型超市。
從司機到某雜志的總編,到廣告公司老板,再到突然移民,陳先生人生道路的每一步都讓他的同學吃驚。“半年前,好久沒聯系的他突然告訴我自己移民了。”陳先生的初中好友朱先生說,趁出差的機會,准備探望一下老同學,剛從墨爾本機場出來,坐上前往市內的機場大巴。
幾番溝通,陳先生還是沒搞懂機場大巴的終點站在哪,離自家有多遠,該怎麼去接同學。最后,在熱心路人的幫助下,朱先生才得知,自己要去的地方離市區還有將近30公裡,最好的辦法是坐火車,而陳先生還根本不知道墨爾本有火車。
原來,這大半年來,由於忙於籌備開店和聯系8歲的孩子上學,加上英語能力不強,陳先生還沒來得及熟悉墨爾本市區和周邊的環境,沒怎麼進過城。適應環境、經營店鋪、融入社區……對陳先生來說,更大的考驗還在后頭。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