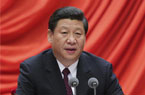解決生產過剩就要縮小收入差距。收入分配體制不合理是市場經濟的通病,但在中國,形成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還有其特殊性,那就是城鄉差距過大,城市化嚴重滯后於工業化,所以推進城市化是縮小中國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舉措。這裡主要是想討論縮小體制中的收入差距需要進行怎樣的改革。盡管難度比推進城市化大得多,但解決體制造成的收入差距問題,已經刻不容緩。
再分配社會財富
體制中的收入分配差距產生於初次分配,即生產成果首先在企業內部分配成歸產權所有者的收入和歸勞動者的收入,還有就是國家稅收以及銀行的利息收入等。收入主要歸產權所有者所有,是調動企業家積極性,從而提高企業經濟效率的基本前提,但也隨之產生了少數人憑借產權而佔有多數社會財富的矛盾,所以在初次分配中效率與公平不可兼得。在傳統資本主義經濟形態中,資本家憑借生產資料所有權,過度壓低工資水平而索取利潤,所以不僅造成了投資與消費的比例失當,導致了頻繁爆發的生產過剩危機,還引起了工人階級的強烈反抗。這也迫使資本主義體系在二戰前后進行社會改良,即運用國家權力改變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比例,從而在不觸動產權關系的前提下,改善了投資與消費的比例關系,兼顧公平與效率。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重大改良,雖然不可能從根本上消除生產資料私有制與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沖突,但的確極大地改善了投資與消費的宏觀分配比例,才有了二戰后西方國家的經濟繁榮與社會穩定。這種市場經濟新體制的出現,正是促使上世紀70年代以來,各國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主要動因。
具體地說,二戰前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稅收佔GDP的比例普遍低於10%,而目前OECD國家的平均稅負在45%左右。提高稅負的主要途徑是征收個人所得稅。1902年美國個人所得稅率平均為1%,個稅佔全部稅收的比例隻有0.3%﹔到1944年“羅斯福新政”改革后,個稅邊際稅率最高已達94%﹔到1950年個稅佔全部稅收比重也上升到29.3%﹔到2011年已超過70%。在全部個稅中,10萬美元年薪以上的人口的稅收比重超過60%,而1%的美國最富人口繳納了28%的個稅,所以美國的個稅主要是由富人繳納的,低收入人口則是從國家的轉移支付中獲得收入。另一方面,發達國家在財政支出中的社保支出普遍佔一半左右,經過這樣的社會改良,社會收入差距就顯著縮小了。
中國既然已經堅定地走上了市場經濟道路,要從體制上解決收入分配差距,就應該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利用國家權力對社會財富進行大規模再分配,而在這方面要做的事情很多。
從全部稅收佔GDP的比重看,中國目前不到20%,要提高20個百分點以上。從個稅看,中國目前佔稅收總額比重不足5%,要提高60個百分點以上,要從目前以產品稅為主的間接稅制,轉向以所得稅為主的直接稅制。目前中國個稅中2/3是工薪階層繳納的,今后要轉向主要由高收入人群繳納,低收入人群則以低保和社會福利等形式,從政府獲得轉移支付。從社保支出佔全部財政支出的比重看,目前剛過1/10,今后要提高到50%。從社保覆蓋率看,目前還沒有做到全民覆蓋,特別是農村居民的社保水平還很低,都需要隨著財政支出中社保支出比重的上升予以解決。
推進體制改革
調整分配關系還必須配合體制改革。因為調整分配關系的難度,其實並不在於要大幅度提升對富人的征稅,而在於這種對分配關系的大調整是否會讓中國的富人相信,這是一件對他們也有好處的事情。西方市場經濟在二戰前后的社會改良能基本上保持平穩,是因為西方生產資料的所有者也同時是政權主體,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相一致。但中國是轉軌經濟國家,在上層建筑方面,相對於通過30年改革已經建立的市場經濟體制而言,還有許多不完善的地方。然而當前中國新興財富階層對能否保護他們的財產權利,似乎有許多擔心。
首先,從香港公司注冊情況看,到2000年才剛到50萬個,到2007年增加到60萬個,年均新增1.5萬個,但到2008年以來開始猛增,至2012年末達到97萬個,年均新增7.3萬個,今年前10個月就猛增了17.4萬個。另據香港公司注冊處的報告,在新增公司中,七、八成是一個人的公司,因此這些企業主要不是想在香港開展經營,而是設立一個窗口。在香港注冊公司的當然不止是內地企業,但內地企業肯定是絕大多數。2008年次債危機爆發后,香港經濟一直不景氣,証明這種注冊公司爆發性的增長並未帶來香港經濟繁榮,很有可能是內地的民營企業家為從內地轉移資本建立外部通道。
內地資本轉移規模大,但這種外移的資本又以FDI的方式轉了回來。中國對外投資額在2008年突然比上年猛增了一倍,到2012年,年平均在800億美元以上。據商務部數據,去年高達878億美元。今年僅非金融類直接對外投資前9個月就高達616億美元,增幅為17.4%。中國企業的對外投資,當然也有相當大的部分是正常的對外投資行為,比如購買企業和資源等,但累計投資中的80%是在2008年以后發生的,所以可以推測,有很大一部分投資是借助對外投資渠道,實現內資外移。
同時,從香港對內地投資比重看,香港回歸前一般在40%,香港回歸后到2003年還出現了33%的低點,但從2008年以后突然大幅回升,到今年9月份已升至65.3%。如果加上海外幾個金融自由港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可看出借助香港和國際金融自由港渠道對中國大陸的外商直接投資,目前已經接近八成比重。此外,2003年中國對外投資隻相當於當年吸收外資的5.4%,到2007年也隻增長到20.3%,也是在2008年以后出現了爆發性增長,到去年已接近80%。
這些情況都說明,2008年以來,有大量中國內地企業借助香港和國際金融自由港建立資本轉移通道,以對外投資或其他方式向海外轉移資本,又以外資形式投回內地企業。如果只是一個方面的數據說明內地存在這種“資本去而復回”的大規模流動,還不足為信,但香港的注冊公司猛增、中國內地企業的對外投資猛增,以及香港和國際金融自由港對中國內地的直接投資猛增,這三方面互相關聯的數據都出現在同一個時間段,就說明這不是三個孤立的事件,而是彼此之間有著內在聯系,對這個聯系合理的解釋,隻能是內地資本換了個身份又回來了。如果這個判斷成立,則這種內地資本需要借助境外保護的情況,就說明中國內地市場經濟體制中存在著一定缺陷。
在當今中國,有權貴與資本相結合霸佔和壟斷社會財富。必須看到,“權貴”不屬於市場經濟范疇,現代市場經濟講的是“法權”,即王子與庶民在商品交換過程中地位平等,而“權貴”恰恰是利用公權侵犯私權的不平等行為,是封建社會貴族特權的殘余。
應該說,資本凝結著國力,資本外移會致使國力衰落,經濟增長失去動力,甚至會引發社會的不穩定。
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明確,中國要走徹底市場化道路。生產過剩危機正在向中國逼近,調整分配關系已經迫在眉睫,大改革時代再不到來,中國就沒有辦法擺脫危機。所以改革要和危機賽跑,可以利用的時間可能已經不多了。(王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