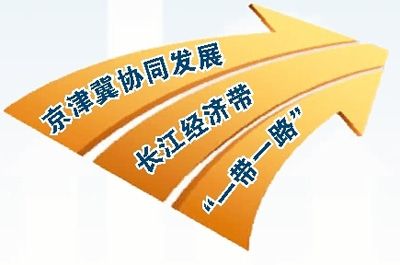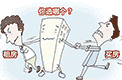[导读]她叫小院,可院子里的人思考的是中国最根本的问题——如何解决“三农”问题;探索的是最有价值的路径——如何实现农业科研与生产实践、科研人员与农民、科研院所与农村的无缝链接与互动;回答的是知识分子必须回应的时代命题——能够为解决“三农”问题实实在在做些什么?
河北曲周第一个科技小院
研究生冯霞在做培训。
慕尼黑大学教授带领师生与科技小院联欢。
本报记者朱先春冯克白锋哲李纯
你知道科技小院吗?
她如一粒火种,从2009年在河北曲周县白寨村诞生开始,就将农业科研、技术推广、学生培养深深扎入广阔的土地与农民中间,尽管火光微茫,却释放着巨大的能量。
她像一条纽带,连接着高校老师、在校研究生、农技推广者和广大农民,连接着众多热爱农业、想干些实事、致力于解决“三农”问题的有志之士。
她是一个平台,在这里实现了多种功能的聚合,大学生认识了农村、服务了农民、成就了自身,高校进行着科研、应用、育人、服务社会的完美结合,农民提高生产技能、发展合作组织、完善乡村治理、活跃文化生活……
7年时间,她已成长为一个顽强的生命体——
从最初只在河北曲周、吉林梨树、黑龙江建三江,到广东徐闻、广西隆安、海南海口、山东乐陵,再到后来河南、江苏、重庆、安徽等地纷纷主动上门取经希望把小院开到当地,而今小院已走出国境,开到了老挝;从最初只是小麦、玉米、水稻的科研推广,到如今拓展到西瓜、苹果、小枣、菠萝、香蕉等多种作物的研究服务;从最初只是由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植物营养科研团队发起创办,到如今联合本校其他专业、各地高校院所、企业和农技推广机构协同参与……生生不息,渐成燎原之势。
她叫小院,可院子里的人思考的是中国最根本的问题——如何解决“三农”问题;探索的是最有价值的路径——如何实现农业科研与生产实践、科研人员与农民、科研院所与农村的无缝链接与互动;回答的是知识分子必须回应的时代命题——能够为解决“三农”问题实实在在做些什么?
有一群人,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团队的师生们,他们选择了科技小院。这条路,充满了苦和累,却通往最深沉的快乐。
1.源起一个小学科的生存欲望
说到科技小院,就不能不提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的张福锁和李晓林。
故事要从1990年说起。
这一年,主攻植物营养专业的张福锁和李晓林先后从德国留学回国。植物营养学是什么呢?学术定义是研究植物对营养物质的吸收、运输、转化和利用规律,以及植物与外界环境之间营养物质和能量交换的学科,通俗讲就是给作物“吃饭喝水”,目的是提高产量和品质。当时在中国农大甚至在资环学院,相对于土壤学、农学、农经等,植物营养还是个“新、小、弱”的学科。
有人说,植物营养不就是一把肥料吗?那个时候肥料紧缺,要走后门才能买到,肥料企业也不关注植物营养,学科和大生产也没有挂上钩。他们就在温室、实验室里做基础研究,逐渐组成了核心研究团队。李晓林笑着说:“我们研究的主要是作物根部以下的事,团队成员最早都是‘地下工作者’。”
经过10年潜心研究,到2000年的时候,团队已经发表了不少论文,开始在国内外有了一定影响。2005年,团队“提高作物养分资源利用效率的根际调控机理”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标志着中国农大植物营养学科在基础理论研究领域有了一席之地。
学科有了一定基础,也得到了国内外同行认可,接下来该怎么发展?早在2003年,张福锁就有了考虑:“除了继续做好基础研究,还应该在生产上有所建树。国内高校基础研究与技术应用存在脱节,科研一定要和生产实际相结合。”2006年,张福锁率先开始重心转移,一方面搞基础研究,一方面开始承接地方的生产科研项目。2008年,团队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把理论向技术推进了一大步,并组建了以资源高效、作物高产为目标的“双高农业技术”研究团队。
这20年的点点滴滴都装在李晓林脑子里:别人老说,张福锁、李晓林你们做基础研究行,到生产里真的有用吗?中国粮食生产有农学,到了地里你们干得过农学院?我们自己也有质疑,虽说得了自然科学奖和科技进步奖,但是研究成果到地里真的有用吗?我们开始跟自己较劲,做基础研究我们逐步跻身世界先进团队行列,能不能在农业生产里面也发挥一些指导作用,为国家、为农民做点实实在在的贡献?另一个压力是,基础研究的经费来源是国家基金,主要保重大项目,我们这个小学科经费少,难以维持越来越大的队伍。
“如何突破学科发展瓶颈?只有到农业生产的主战场去。而做生产就得下地,不下地,瓶瓶罐罐种不出高产,种不出农民需要的东西。谁去下地?大家都犹犹豫豫的,因为做基础研究轻车熟路,但对大生产还是陌生,怀疑自己会不会到大海里面被淹死,没有人敢一下子扑下去。经过两三年酝酿,学科的主要老师不断讨论发展方向、加深认识、形成共识,思路越来越清晰了。”张福锁回忆说。
2009年,思考终于变成了行动。促使他们下决心的契机,是那个时候植物营养学团队承担的几个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的结题时限。李晓林回忆:“我承担的黄淮海中低产地区课题里面有一项5万亩的示范任务,2010年要交差,但2009年初用于示范的地块还没有落实。有人说,李老师,不用急,你把技术方案交给地方,到时候给你出个推广证明、盖个章就可以了。我们做基础研究的有点较真,不是自己干的心里不踏实,总觉得盖个章就完事了,这样干我脸红。”
促使他们“下地”的另一个原因,是2009年全日制研究生培养改革启动,开始招收专业硕士,中国农业大学是首批试点。传统的研究生教育重在培养学术能力,查文献,写文章,主要在学校进行。理论与实践、研究与应用存在脱节,学生接触生产机会少,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足。当时,全国有60多万名硕士生,国家意识到,都去搞基础研究是浪费人才。而专业硕士就是为了培养研究生的实践动手能力、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培养社会需要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刚好要下地了,也不知道‘专硕’该怎么培养,我们就想借这个机会试试。”李晓林说。
当时,张福锁决定兵分三路。江荣风教授带队到黑龙江农垦建三江管理局,那里是现代化大农业,是重要的水稻产区;米国华教授带队到吉林省梨树县,那里人均六七亩地,代表中等规模农业,是重要的玉米产区;李晓林的课题研究地区是黄淮海中低产区,就带着张宏彦、王冲两位老师到了曲周县,那里是小麦—玉米轮作地区。人均一亩半地,地块分散,属于传统的小农经营,这是中国绝大多数的农业经营方式。
2.出师受阻,偌大的平原找不到一块实验田?
选择曲周,是因为曲周与中国农大有30多年的合作历史,1973年石元春和辛德惠两位院士就在那里搞盐碱土改良,有中国农大的实验站作依托。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却出乎曲周小分队的意料,困难接踵而至。
第一个阻力来自于实验示范地块难以落实——
他们到曲周后想做一个示范方,让农民用上中国农大获得国家奖的高产高效技术,用最少的肥料代价换得最高的产量。我国农业科技体系分工是大学主要做基础研究、科研院所主要做应用研究、农技推广部门负责推广。当时,县里举行了隆重的启动仪式,县领导表示要全力配合张福锁团队把高产高效万亩示范基地建好。
领导很痛快、很支持,具体落实起来就没那么简单了。李晓林带着两位老师去找农业局局长、土肥站站长。都说这事挺好,让农民增产增收,还少用肥,保护环境,但说归说,却一直按兵不动。
“我好赖是中国农业大学的教授,局长还是我们系主任的老同学,土肥站还和我们是一个行当啊!一笔写不出俩肥字儿,怎么这么不帮忙!”李晓林很受刺激、很不理解。
而多次接触后,才发现他们的难处。站长说,我们承担了好多项目和任务,整天忙得团团转,你们这个事我们是很想帮忙,可就这么几个人,条件也有限,一出去就是一二十公里,怎么去怎么回?我们也不愿意天天在办公室坐着,可一出去就得有车,开车就要烧油,就要花钱,经费有限,实在没办法。
之前,资环学院有两次想在曲周开展一些大的项目,结果都碰到同样的问题:地方推广部门没时间或者没精力,毕竟教授们写论文和人家没有太大关系,作为朋友可以帮忙,总不能天天帮。
“怎么做点事就这么难,不行回去算了,回农大自己在温室里弄几个盆弄点肥料我自己都能控制。走还是不走?犹豫半天。但想到课题第二年必须完成,不能真打退堂鼓呀,得想办法。”李晓林说。
于是,张福锁、李晓林就开始自己在实验站周边寻找示范田。那时候,附近竟然没有一块50亩以上的小麦地,全是棉花。因为这里盐分比较多,历史上都是以棉花为主。他们只好开着车四处转,找啊找,一直找到城南5公里的白寨乡,那里有四五万亩成片的小麦地。虽然实验站在城北,离这儿有20多公里,也没有更好的地了,只好选在白寨乡的白寨村。
当时有县领导对张福锁说:“张院长你们别费劲了,你们让农民种,农民也不听你们的,就是召集开个会都很难,更别说组织他们干活了!干脆通过县里把示范方几百亩地流转过来,你们给点实验费,统一种多好。”张福锁说:“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在北京就行,何必来曲周。我们是想让农民自己真正把技术用起来,自己增产,这样才有生命力,才能传播下去。我们不是要在这里做一个样板给别人看,是要了解其中的过程,这些技术到底能不能用、怎么用,用的中间有什么问题,根据这些去优化技术,真正实现大面积的高产高效。”
地找好了,另一个阻力又来了。农民对教授们的技术很消极——6月初小麦收了,第一季实验就从玉米开始。“我们把高产高效技术讲得很细,用什么优良种子、什么肥料,怎么施肥,想让农民跟着我们的指导做。想得挺好,但是做起来那个难呀。”李晓林说到这里直摇头。
他们在万亩示范方里选了一块地,准备打造成核心示范方,周围选上一系列示范点,先做给农民看。核心方是163亩地,一共74块地,一块地最多4亩,有的一小条才5分地。“100多亩地要是自己开拖拉机两天就能播完,怎么着3天也能播完吧?但是到最后,农户都是自己种、自己收,机器也是自己联系,整个过程持续了11天!我们发现农业生产并不像原先想的那么简单,第一次深切体会到一家一户分散经营效率这么低。”
为了做好示范方,李晓林他们要给74户农民开会,统一品种,统一肥料。光开会还不行,还必须盯着每户农民才能按照实验方案种下去,否则他们按照自己的干,那实验就白忙活了。
农民早上5点半就到地里干活了。李晓林他们租了一个面包车,早上5点从实验站出发,天天到地头等着,督着农民把肥料称好弄到播种机上。上午10点多,农民都回家了,把他们丢下不管了。第一天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没人了?第二天问农民:“昨天你们干吗去了?”
“我们回家睡觉了,下午4点天凉快了才来。”
当时正是暑伏天,李晓林他们没地方去,也不能回实验站,只能找个树荫处干等着。刚到农村,他们对农民的作息规律一头雾水,不知道农民什么时候回来,都不敢离开。
村里说,教授种地那么麻烦,我们自己种不就完了嘛!闹得农民老大不高兴,也不管他们饭。到镇上又太远,李晓林和学生就在城里买点饼带到地头吃,三天后全拉肚子了。到第五六天,身体受不了。
李晓林说:“那时觉得那个惨哪,什么破教授啊,真是不值钱!农民眼里没教授,别看你在学校里耀武扬威,到这儿啥也不算,这种落差也太大了!我们还好办点,年纪大无所谓,学生拉出点病来怎么办,家长饶不了我们。我就开始琢磨怎么解决,没有个落脚点不行,住实验站也不行。住在实验站,早晨来、晚上回去了,跟农民接触少、缺少互动,我们不了解实际情况,农民也不知道你干嘛。得要到农民中间去,跟他们交朋友。”
到了第七天,李晓林他们发现,自己遇到的这点事儿不算难不算惨,农民种地才更不易更可怜。玉米早种一天每亩就可以多收十几斤的粮食,可为什么3天的活要干到11天?因为正是旱季,必须马上浇地,有水以后玉米籽才能发芽,要不然出不了苗。当地浇地只能靠地下井水,而井的数量有限,村民先找管井的抓号,再按号排队轮着浇。可能一方地里,最东头的抓了第一,第二号到了最西头,一条水管弄过去弄过来,耽误很长时间。接连几天早上,看到好几位农民在地头躺着睡觉,李晓林问:“在这儿睡了一夜?”
“是啊。”
“比家里凉快?”
“什么凉快啊,我排队呢。”
原来,比方说你排到4号,3号晚上12点浇完地了你4号必须接着开始浇,要是你人不在这儿直接到第5号了,那你就得重新排。就为了浇这两亩地,农民只好睡在地里。
在跌跌撞撞、磕磕碰碰中,163亩核心示范方种完了,李晓林也下了决心——必须驻村!
3.第一个科技小院艰难诞生
大家一起讨论,有年轻老师说住实验站多好啊!按三星级宾馆装修的,有空调,有电视,有食堂。不行住乡里吧,条件可能要好些。到乡里一看,没地儿,只能驻村。
到村里住也得找乡书记。这事又给人添麻烦,一起吃个饭吧。“李老师,先不说别的,先喝酒。”书记很热情。“我不喝酒。”
“你把这杯酒喝了,我想办法给你找一个小院,让你住下来。”
李晓林喝酒过敏,到现在也喝不了,但为了能有个安身之地,豁出去了。一小杯白酒下肚,他的脸马上就红了。
“你还行,不错。”书记说着又倒一杯,“你把这个喝下去给你两个小院。”第二杯下去,李晓林马上天旋地转,不行了。
“李老师真的不能喝酒,原来不是开玩笑的,行了,喝了两个,我给你找两个小院。”
到了下午3点多钟,缓过劲了,李晓林他们赶紧找书记。“你说那个事还有戏吗?”
“有戏,找办公室主任带你看看去。”
说话真算数。到小院一看,他们彻底心凉了,原来是乡司法所在白寨村有一排房,长期没用,院里的草有人那么高,地上全是狗屎猪粪。没办法,他们把草铲掉了,地面打一打平,屋里重新刮了,又买了桌子、床,第一批人——李晓林、张宏彦、王冲3位老师和曹国鑫、雷友两名研究生就住了进来。
问题又来了。曹国鑫女朋友给他写信,连地址都没有,谁来找也不方便。起个名字吧,叫什么呢?大家一议,我们不就是到这儿做科技的吗?就叫科技小院吧。
科技小院就这样叫起来了。
那时候,他们还没有意识到科技小院这几个字的作用。半年以后,邯郸市科技局局长到曲周来调查走访,无意中听说农大的老师和学生们在这里,就到了科技小院,聊了一两个小时。他说你们扎根农村,和农民同劳动,培训传播技术,培养学生,做实验做示范,这个挺好。科技小院也很有特色,与农民没有距离,住在村里面解决农民的问题,这个很接地气。
局长回去以后,上网查“科技小院”,没有这个词。没有就是新东西。2011年,邯郸市委市政府授予李晓林“邯郸市十大科技创新人物”称号。
“我们的技术获过国家级大奖,团队发明的方法上过国际版教科书,我觉得这些才算创新。但在这儿住了两年多,科研的事没怎么干,我创新在哪儿?局长说,我们给你荣誉,就是因为教授住在了农村,这就是创新。中国现在最需要教授专家们到生产一线,到村里来,想老百姓的事,干老百姓需要的事,这是最大的创新,这个时代需要这样的创新。我说那倒是,我一年在这儿住了280天,你这么夸我,我还是能接受的。”李晓林说。
1234下一页 1234下一页
| 下一页 |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