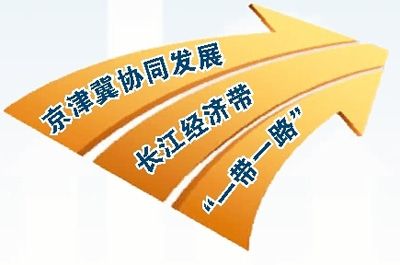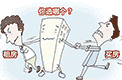路變化很快,可人變化很慢
1068個黃白相間、屋檐彎彎、貌似木頭實為水泥的新安居房建造了起來,獨龍族人告別了茅草房。
獨龍族人王世榮的家,用上了大理石的茶幾,玫瑰花圖案的沙發、窗帘。一個開小賣部的村民,家裡還貼著林志玲的畫。80歲的老人學會了用上海人援助的電飯鍋。每人每年分到370斤糧食。
這個援建方案,不知道改了多少稿。上海專家曾為獨龍鄉設計的房子有很好的廁所。可村民告訴他們:我們祖祖輩輩沒用過廁所,不需要。最后,圖紙改了,修成公廁。
雲南扶貧辦的牛濤說,扶貧工作做得越久,越發現尊重當地人的想法是重要的工作原則,無論他們的想法多麼奇怪。
如今獨龍江鄉成了怒江州最富有的鄉鎮。別的鄉鎮都有些羨慕獨龍族的“獨”了。
可變得最慢的是人。以前獨龍族人每天上午11點才吃早飯,現在,上午9點村裡便會響起起床廣播。5年來,雲南抽調了118人次進駐獨龍江鄉幫扶,對村民們從怎樣上廁所、怎樣洗澡、怎樣掃地、怎樣種菜開始“培訓”。
獨龍族人也常三三兩兩聚在小賣部,晒著太陽,用獨龍語規劃未來“藍圖”,比如他們要禁止賣瓶裝酒了,因為玻璃不能分解,“山神會不高興的”。偶爾,他們也開玩笑,嘻嘻哈哈地憧憬著:以后人來多了,你當駕駛員、我撈魚、他賣洋芋……
有些變化,獨龍族人自己都不能察覺。據新華社報道,一位叫畢珍蘭的婦女成為獨龍族歷史上第一個賣菜的人。山外來的幫扶干部在當地辦起蔬菜大棚,菜種出來了卻找不到人賣,因為獨龍族沒有經商的文化。后來,干部找到畢珍蘭,讓她去試一試。
“她背了一背簍菜到街上,菜不擺開,也不招呼人買,下午把一簍子菜又背回來了。”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幫扶干部李發朕生動地介紹了畢珍蘭當時的生澀。
最近大家說得最多的是,幾個獨龍族人上電視了。有人笑,一個文面老人被安排去昆明見“習大大”,因為從沒坐過汽車,一路暈車,不得不“很不爭氣”地中途到縣城輸液。
還有一個從沒出過遠門的文面女,在見“習大大”前,臨時“培訓”怎樣上飛機、上廁所、坐電梯,怎樣走地毯不摔跤。
見了習大大,沒說一句話,也沒得到一個鏡頭的鄉長一直被人嘲笑,“太膽小、沒見過世面”。
這個春節,也是獨龍族歷史上第一個沒有大雪封山的春節。
在貢山縣城讀小學的王燕玲,第一次回獨龍江鄉過春節。往年,在縣城讀書的獨龍族孩子,隻能在暑假回家,在親戚家、學校過寒假。
這個雙子座、喜歡TFboyd 的女孩說,她還是更喜歡外面的世界。
在貢山工作的獨龍族人李金榮,今年也是第一次回獨龍江鄉過年。他在“獨龍老鄉”微信圈裡寫道:“我們回家了,老賽開勒羅尼窮能阿肋秀。”(獨龍語:回家過年的感覺真好)
就像這個水裡有點點茶味道就夠了
李金明不久前也回了趟獨龍鄉,他感慨回家的路“太快了,快得不習慣了”。
他主張修路,卻反對開發。
每次聽到有人說“獨龍族多麼多麼落后”,這個瘦小的學者都跟人急:先進與落后很難區分,獨龍族沒有一個人餓死,大山裡到處是寶貝。文化沒有落不落后之分,只是生活方式不一樣。
戴著插有羽毛帽子的李金明說,獨龍族一步從原始社會過渡過來,關於他們的發展,要多聽聽他們的聲音,也要讓社會批評的聲音存在,不能讓一種強勢的力量,“一腳就碾過去”。
盡管這個在雲南社科院15層大樓裡工作的學者,看起來似乎“唯物得很”,可一進村,就像換了一個人。像小時候一樣,他相信神的存在:路過拉索橋、懸崖、古樹,他會禱告不要讓人掉下去。他甚至相信“沒有偷東西的人,手放在油鍋是不會燙傷的”。
他眼見著路快捷了,可過去的村子越來越遠了。如今,村子裡有戴著頭盔酷酷的飆車少年,有生意不錯的台球室。婚禮上,年輕的姑娘不再穿著七彩的獨龍服,而是穿著白婚紗。年輕人學會了照相時,伸出兩個指頭比劃v。隨著外地人的增加,部分道路旁邊的門也會上鎖。
在他看來,“要命的手機讓年輕人更遠了”。 他小時候,一有事,全村人聚在一起商量,甚至用短木棍投票的場景,再也沒有了。
獨龍江2004年開通手機信號時,每次隻能容納15人同時通話,第16個人需要走路4公裡去找信號。如今,這裡通了4G。
他很理解一個人封閉太久后那種對新空氣的渴望。就像小時候,馬幫進村子放電影《地道戰》、《南征北戰》,大家都聽不懂普通話,可很快,孩子們都在森林裡挖起了地道,當上了“好人”。
他擔心獨龍族的文化會一點點消融掉,變得隻剩下“博物館意義”。
上世紀90年代,他曾借錄音機、照相機,找村裡的老人講故事,留下了40多盤磁帶,因為沒有經費,這些珍貴的資料至今沒有轉化成數碼資料。
他端著碧螺春茶說,擔心也沒用,我們能做一點算一點,“就像這個水裡有點點茶味道就夠了!”
植物學家李恆后來也數次背著糖果、香腸進獨龍鄉,她發現,孩子們不愁吃喝了,鞋子多得穿不完。
獨龍江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接受教育,有些出去的人不再願意回來。
有媒體報道,清華大學趙麗明教授2008年曾在獨龍江做過調研,她雇了雄當村村支書陳永華為向導。讓她沒想到的是,一進陳家家門,陳永華的老母親就拉著她的手,請她幫忙尋找自己的小兒子。
陳永華的弟弟在昆明讀完大專后就再也沒有回過家,母親太思念兒子,逢人就問。趙教授為老人家錄下視頻,並請學生放到網上。1個月之后,居然找到了。
“隨著經濟的發展,獨龍人也在傳統與現代的生活方式中尋找自己的位置,但需要時間去適應現代的生產方式與生活節奏。”趙麗明說。
這些年,貢山縣政協副主席豐衛祥一直在做一件事,在獨龍江鄉尋訪健在的紋面女,為她們拍照。
豐衛祥一共找到了68個文面女,其中包括李金明的母親金妮。如今,這些照片編成了書,可送書時,很多人都不在了。
“前年還有38個文面女,到去年就隻剩31個,現在隻有28個了。”每當有文面女的家人來派出所銷戶口,大家就特別難過。
有人推算,十來年后,中國最后的文面女也將成為歷史。
李金明還記得在北京讀附中時,為准備一個節日,他們每天在烈日下訓練三四個小時,看到一些女生中暑昏倒了,體弱多病的他告訴自己,“不能倒下,千萬不能給獨龍族丟臉啊。”
如今,沒有在電視上露臉的獨龍江鄉鄉長,一直耿耿於懷,他希望能拿到和習大大的合影。
最近,“老縣長”高德榮得了嚴重的骨質疏鬆,走在翡翠般碧綠的獨龍江邊,顯得更矮、更小了。曾有人和高德榮開玩笑:“你個子不高為什麼還姓高呢?”高德榮笑著說:“我站在高黎貢山上,為什麼我還不高?”
穿著牛仔褲的86歲的李恆,每天仍然去辦公室工作,去年,她獲得了國際天南星植物學會的最高榮譽獎勵。她說,“科學沒有止境,人類連玉米都沒研究透呢”。
這個世界上不超過一萬人能聽得懂的獨龍族語的山歌常常在高黎貢山山頭響起:
我們在樹林子裡唱過的歌,
被虫子寫在樹葉上了﹔
要想反悔呦,阿哥
去問問那寫字的虫子……
獨龍江村子之間都通了水泥路,隻有一條路沒有水泥,路邊的野花在怒放,手掌模樣的藤蔓四處延展,它通往墓地——那裡埋葬了8個戰士,墓碑沒什麼樣式,粗笨的橢圓形,它們距離國境41號界碑很近,8個人中有的就是為修路死的,最小的僅18歲。
墓地是前幾年修成的。一次,邊防派出所的所長在回獨龍江鄉的客車上,遇到了隧道工程指揮部的一個處長,兩個不相識的男人沒說太多話,所長問處長要了10噸水泥。
幾個月后,這10噸水泥全部變成了墓碑。這時,距離最早的一個修路的戰士犧牲,已經幾十年。記者 從玉華
| 上一頁 |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