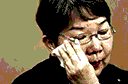四、深刻理解投资的战略地位,防止“悬崖式”的调控
固定资产投资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推动力量,2010年以来对GDP增长的贡献在三驾马车中占比一直保持在50%上下。在目前国际经济缓慢复苏、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偏弱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想要稳定在合理区间,仍然需要适当规模的投资强度,对投资驱动力既不可过度依赖,但也不能盲目“去投资化”。应在逐步淘汰落后产能的基础上,对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将投资增速稳定在20-25%左右,避免投资增速出现“悬崖式”跌落。
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仍然存在严重的基础设施不足问题。基础设施投资在国际上也成为经济增长战略的重要部分。美国近年来多次提到要建立基础设施银行;2013年欧盟委员会通过了《绿色基础设施:提高欧洲的自然资本》的新战略;2013年日本提出“新增长战略”,计划未来十年内将公共设施投资增加50%。麦肯锡预计,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在未来18年间要达到57万亿美元,中国仍将是全球最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国。但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在投资发挥战略支撑作用时期,必须把握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确立市场在资源配方面的决定性地位。一方面利用市场机制在淘汰落后产能过程中,倒逼相关企业尽快适应,主动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下放行政审批权,降低政府对投资的主导作用,调动民营资本投资,尤其是要放开一些行业限制,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激励民间资本活力。还要防止短期内在某一领域集中、过度投资,形成投资的低效和浪费,政府部门应将有限的投资投向那些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增长、对经济拉动作用更为持久的基础领域和民生领域,重视引导非政府部门的投资方向,与政府投资形成互补。投资调控政策的重点要向支持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支持产业转型升级、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推进城镇化建设和区域协同发展等倾斜。
第一,支持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科技创新是解决经济发展诸多瓶颈的关键,应该将推进重大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作为投资政策的重点,政府和企业都应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并实现科技成果尽快投产,提升现有产业的技术水平,并催生新产业形成与发展,充分发挥“科技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参考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做法——其在第一个预算方案中,将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部科技办公室等重要机构的研究费用翻了一番,并向企业技术研发提供税收减免740亿美元,并计划未来10年将基础研究资助翻一番,这些措施虽然不像基建投资项目那样直接带动GDP,但是保障了美国支柱产业(信息技术、高端制造、农业、医药、军工等)的长期核心竞争力,促使若干新兴产业领域(页岩气、3D打印、新移动网络和移动媒体、环保设施、电动和无人驾驶汽车等)的产生。
第二,支持产业转型升级。发挥中国产业的后发优势,向发达国家借鉴吸收一流生产技术、服务和管理经验,并努力培养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农业方面,推广现代化设施、工具和运营方式,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工业方面,积极推广信息化和流程优化管理,升级生产设备技术,提高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减少低水平建设,引导淘汰落后产能,引导生产力的科学布局和产能的有序转移,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推广节能减排技术。金融服务业方面,应加快金融结构调整,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重点发展直接融资、风险投资、战略投资等融资模式。
第三,激发民营投资活力。进一步完善民间投资政策措施,引导民间投资进入基础产业和支柱行业等领域,最大限度放开准入限制。继续强化对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扶持,进一步明确财政金融政策。引导民营企业做优做强,形成品牌优势,培养核心企业,以大企业带动关联企业形成更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第四,稳步推进城镇化和区域协同发展。以城市群建设投资为重心,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协同发展。围绕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部署,合理安排国家投资方向,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水平,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改善城市人居生态环境。引导投资和其它资源在土地综合整治、安置房建设、新城区建设、城镇棚户区和旧厂房改造、产业园区建设以及各类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交通、通信、水电煤暖)等领域的合理配置。
| 上一页 | 下一页 |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QQ空间










 恭喜你,发表成功!
恭喜你,发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