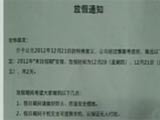現年32歲的夏劍峰原本在上海金山區一家醫療用品企業工作,年收入兩三萬。7年前,他回到金山區高樓村做農民﹔今年,他種植的草莓和西甜瓜大約能帶來50萬元利潤。
“那時,老婆去了趟日本,回來說起日本的農民,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能把農產品賣出好價錢。”這和夏劍峰對“農民”的理解大相徑庭——在他出生成長的農村,幾乎所有“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年輕人都去了城市。辭職后的夏劍峰開始用不同於父輩的方式務農——更接近於“工人”甚至“經營者”。
現代農民“金山草莓哥”
夏劍峰關於“現代農民”的抱負,從30畝左右的“家庭農場”開始。承包一定規模的土地,以家庭勞力為主進行農作物的種植、經營,這就是正在滬郊興起的“家庭農場”。
金山區農委主任張亞軍介紹,金山區的農村土地流轉比例已達79%﹔土地流轉使離土農民收入多元化,也為上海發展現代農業創造了條件——滬郊力推的“家庭農場”正是規模化經營的探索。“上海的家庭農場和美國的大農場不一樣,不是越大越好,而是採用‘適度規模’。”他解釋,南方農村土地高度分散,客觀上限制了種植戶規模的無限擴張﹔考慮到農戶的經營能力和風險承受能力,也建議把種植規模控制在家庭可承受范圍內,“在金山區,糧食種植以200畝到300畝為宜,經濟作物種植以30畝為宜。經營能力確實出色的,可以放寬。”
夏劍峰聘請母親曹友芳擔當家庭農場的“技術指導”——曹友芳種了20多年西瓜,是有名的種植高手﹔自己負責營銷和整體運作。去年開始,除了種西瓜,他還種草莓,並在微博上管自己叫“金山草莓哥”——很多人因此認識他,在網上下單,甚至打聽了草莓大棚的地址,直接去現場採摘。今年的草莓季剛剛開始,夏家20畝的草莓預計能帶來50萬利潤。明年,種植面積將擴大到70畝左右,因為夏劍峰和周邊鎮上的十多個農戶組建了種植合作社,而農戶們都希望明年能從他那裡引入草莓苗。
“一定是沒人種田了”
夏劍峰的父母曾經極力反對他回家當農民,“他們覺得,做農民非常辛苦”。但夏劍峰認為農民離開土地的原因不是怕吃苦,而是由於產出和投入不成正比,“同樣的付出,在其它行業換得的收入遠遠超過農業——隻有等投入產出比變得合理,農民才會是大家眼中一個有質量、有前景的職業。”
50多歲回歸農業的沈鐵剛吃過種地的苦,比夏劍峰更能深刻理解這一點:“每戶都隻有幾畝地,一年忙到頭,每畝地最多不過掙幾百,何苦呢?”5年前,金山工業區農技中心找到沈鐵剛,建議他嘗試承包“家庭農場”,當時在做水泥工的他腦海中蹦出一句“一定是沒人種田了”。
其實,當時的上海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正逐漸規范和完善,農戶可將土地流轉到村集體或政府搭建的土地流轉平台,由村集體租賃給規模經營戶,或由流轉平台招商引資,租給有需求的農業企業。曾經是種植能手的沈鐵剛被視為承包“家庭農場”的最佳人選。
回來“種地”的沈鐵剛和兒子共同經營著910畝水稻田,每天早上5點起床,循例繞稻田查看一圈——這一圈得走1個小時。盡管還保留著早年務農時的作息,但鄉鄰們眼中的沈鐵剛已“大不一樣”:他平日裡穿著黑色呢大衣、西裝褲、皮鞋﹔他的農場有3台拖拉機、4台收割機、2台插秧機,幾乎實現了全程機械化種植﹔他不按照1.5元一斤的收購價把稻谷賣給糧管所,也不賣兩三元一斤的散裝大米,他賣的是包裝好的“品牌大米”,每10斤60元﹔他還雇佣了八九名鄉親做幫手……“因為,他有技術,還懂營銷。”
但沈鐵剛的絕大部分土地是“流轉”而來:每一年,他為每畝流轉地支付808.5元的租金﹔除去土地租金和其他成本,每畝地每年的淨利潤是500多元,“隻有3畝地的時候,這些收益不算什麼﹔如果有300畝地,就很可觀了。”
“會有大學生來種田的”
“推動規模化種植,追求規模效益﹔推進農業機械化,提高勞動生產率﹔加強政策扶持和農業保險等市場手段的應用,強化農民的抗風險能力……這些手段,歸根結底是為了提升農業的投入產出比,讓‘農民’這個職業擁有更高的含金量。這也是改變農業空心化的一種途徑。”張亞軍告訴記者,農業的現代化對從業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為一種職業,農民要有職業技能。”
目前,金山區正在開展“百千萬工程”,目的是培養100名杰出青年農民、1000名新型專業農民、10000名現代農業產業工人,讓一批“年紀輕、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有潛力”的青年來推動農業組織化、產業化發展。
夏劍峰是百名杰出青年農民培訓班的學員,他仍然無法向父母描述他對“農產品附加值”和“農業產業化”的種種想法﹔但他相信,“今后一定會有大學生、研究生來當農民。”
-現代農民眼中的就業質量 未來的“農業產業工人”
56歲的沈鐵剛曾經很悲觀:比他年長的人無力學習先進的種植技術和農機操作技術,年輕人則“絕不可能回來種田”,“以后沒人懂種田了。”
32歲的夏劍峰說得很坦率:如果農業的投入產出比無法提高,那些“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年輕人就不會把農民當做職業﹔那麼,誰來發展現代農業,提升農業的投入產出比?不過,他們此刻所做的事,正在改變農民的定義:成規模地生產,還嘗試做運輸和營銷。他們還用自己的收益証明,農產品也可以有很高的附加值。他們,就是未來的“農場主”或者“農業產業工人”。
上海郊區的農民們告訴我們,農業領域也可以有高質量的就業,農民也是有前景的職業。(記者錢蓓)
(來源:文匯報)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