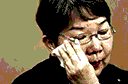省際競爭的外部驅動力和存量改制的內在驅動力,是區域模式選擇的兩大主導因素
長期以來,有關江蘇模式和浙江模式的爭論,一直是人們熱議的話題。其實,沒有哪一種模式是獨立存在的,也不存在哪一種模式一定就好的問題,關鍵是看是否存在該種模式適應的條件。比如,江蘇私營經濟的發展過程,就與“政治約束”的鬆緊和反復相聯系。在20世紀80年代私營經濟隻能成為“補充地位”並糾纏於意識形態爭論時,浙江是民營經濟起步和快速發展時期,江蘇則大力發展以集體經濟為主的鄉鎮企業﹔當80年代末、90年代初私營經濟升格為“並存”和“共同發展”地位時,浙江處在民營經濟快速發展和全面發展時期,江蘇則借助於浦東開發開放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
目前,以外資開放為代表的江蘇模式和以民營經濟為代表的浙江模式,正在逐漸走向融合。在全國民營企業500強中,江蘇民營企業的規模遠大於浙江﹔浙江的外資規模尤其是浙北的外資規模現在也很大。以2011年為例,500強中,江蘇有118家企業入圍,上榜企業的營業總收入達19082.46億元,佔500強營業總收入的27.32%﹔上榜蘇企資產總額達13454億元,佔500強資產總額的22.87%,兩項指標的絕對額和佔比均位居全國第一。
區域的模式選擇,具有強烈的路徑依賴特征。省際競爭的外部驅動力和存量改制的內在驅動力,是兩大主導因素。兩種模式的路徑選擇和基本經驗,可以概括為以下方面:第一,制度創新和變遷是全面解讀模式選擇的總綱和邏輯主線﹔第二,改革開放是全面提升模式經濟實力的動力之源﹔第三,企業加入集群、集群加入全球價值鏈,為模式發揮作用提供最重要的交流平台和載體﹔第四,根據市場變化選擇主導產業、調整產業結構、提升產業水平,是模式發展壯大的動態特征﹔第五,通過各種軟硬件基礎設施的優先增長來引導產業空間均衡布局,是兩種模式發展作用的保障措施。
江蘇模式的演繹,三個方面的因素不能忽視,一是改革中對最小政治風險的選擇,二是強勢政府的有力推動,三是次生性制度創新的靈活運用
制度變遷是全面解讀模式選擇的鑰匙
從根本上講,區域發展的模式選擇和結構變遷,除了區位條件的改善之外,最為本質、最為核心的要素就是制度創新和制度變遷。在早期的計劃經濟年代,江蘇和浙江的產業發展主要是服從國家整體發展的戰略需要,但在轉軌經濟的早期,江蘇主要是模仿性、次生性的創新,浙江更多的是帶有原創性特點,但在20世紀90年代之后,江蘇原生性創新的特征開始顯現。
江蘇模式的路徑選擇帶有三個根本性特征:一是整體產業發展緊緊圍繞趕超政治而展開﹔二是整體產業布局主要圍繞重工業優先戰略而展開﹔三是社隊企業及鄉鎮工業的崛起和發展。一方面表現為社隊企業的制度創新,另一方面利用上海星期天工程師,幫助企業實現技術創新突破和企業組織結構創新。
與江蘇社隊企業和鄉鎮工業模式不同,以溫州模式為代表的浙江模式,不僅市場機制靈活,對江蘇模式的蘇南鄉鎮企業模式長期存在倒逼壓力,促進了江蘇企業改制。江蘇通過吸收外國資本和發展民營經濟,不少企業搶上了登陸証券市場的“頭班車”。証券市場特有的“江陰板塊”現象,就是一個好的例証。
江蘇模式的成功,正是一次次成功的抓住了從社隊企業到鄉鎮企業,再到民營經濟和外資經濟並重,並借助上市公司資本平台等重大機遇。江蘇模式的演繹,三個方面的因素不能忽視,一是改革中對最小政治風險的選擇,二是強勢政府的有力推動,三是次生性制度創新的靈活運用。
與江蘇模式不同,浙江以溫州模式為代表的民本經濟,早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就已全面超過江蘇鄉鎮企業,浙江企業家逐步橫掃全中國。江蘇民營經濟則起步普遍較晚,可以說在1997年之后,才真正起步發展民營經濟。不過,江蘇是在已經積累了龐大的集體資產基礎上,根據既定的制度約束,來加快對鄉鎮企業和中小型國有企業改制的步伐,走出了一條催熟“次生型”民營經濟、保持經濟增長在全國領先地位的捷徑。
如果說江蘇在發展外資經濟問題上,歷來把廣東和上海作為競爭參照系的話,那麼,在發展民營經濟方面,從1996-1997年開始,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各級地方政府,甚至省委省政府的公開文件和主要領導的講話,都表明江蘇一直緊緊盯著浙江。
正是這種趕超意識和競爭意識,推進了政策創新和制度改進。
浙江的私營經濟是一種自下而上的民本經濟,即由老百姓而非政府創造的民有、民營、民享的老百姓經濟,地方政府充當了降低大規模制度變遷的“摩擦成本”的角色
改革開放是提升模式實力的動力之源
改革開放對於江蘇模式的重要意義,不僅體現在它是制度改革的一次重大創新和突破,還體現在它成功的利用國際制造業外包的機遇,適時的實現了經濟騰飛。
在當時,有一項轟動全國的草根企業經營管理模式改革,就是“一包三改”,即實行經理廠長為主的承包責任制,改干部任免制為選聘制,改工人錄用制為合同制,改固定工資制為浮動工資制。此外,任期目標責任制和內部審計制度,也是頗有影響力的改革舉措。正是這些改革舉措,解決了鄉鎮企業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問題,對於建設現代企業制度起到了一定的借鑒作用。
不過,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短缺時代,這些舉措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體制上的某些缺陷,但對政府過多干預企業的經營行為未能進行有效的約束。由於當時的鄉鎮企業經營權承包做法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產權虛存的問題和弊端,廠長和經理負盈不負虧,盡管后來通過延長任期責任制,通過技術性改良等措施,還是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結束了姓“資”姓“社”的爭論。在此期間,溫州個體私營企業的蓬勃發展,給蘇南鄉鎮企業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在溫州私營經濟崛起之后,蘇南鄉鎮企業被迫開始改制,政府卻成了改制的最大阻力,因為改制削弱的是鄉鎮和村的權力。以當時的錫山市為例,鄉鎮企業晚改制一年,集體資產每年將流失幾十億元。
2000年,蘇南鄉鎮企業改制全面完成。幾乎在同時,以鄉鎮企業為核心的“蘇南模式”正在發生另一種嬗變,以外資模式為主的新蘇南模式悄然興起。可見,新蘇南模式不僅僅是外資模式,也是鄉鎮企業的華麗轉身。在改制中,不少企業通過吸收社會資本成功上市。在產權制度改革方面,江陰起了個大早,鄉鎮企業轉為民營后,不少企業趕上了上市早班車。
江蘇外資模式的關鍵問題是,本土企業嚴重依附於外資企業,雖然一定程度上能夠獲得GDP的增長,但往往存在著技術升級上的巨大障礙,出現了豐收中的貧困現象。2000年以后,江蘇開始反思經濟發展速度高、老百姓可支配收入低,浙江經濟總量較低、居民收入高的事實,開始學習浙江模式,加速發展本土民營經濟。
產業集群是區域模式發揮作用的平台
眾所周知,浙江模式的企業具有“行商”特點,江蘇模式的企業普遍具有“坐商”風格。江蘇的企業更適合給跨國公司代工,浙江企業以自我創業為主。例如著名的娃哈哈,其產業鏈提升的路徑是,由賣水買瓶,到賣水又賣瓶,再到賣水賣瓶,又生產制瓶流水線與模具。
江蘇模式和浙江模式的一個重要共同特點是,為了提高本土企業參與國際生產體系的經濟循環程度,兩地政府均加大了開發區建設的力度,產業集群成為區域模式發揮作用的重要平台。本土企業快速融入國際分工體系,是兩種模式經濟轉型過程中產業空間組織的一種重要的“轉型制度”形式。
市場變化引領產業發展是模式的關鍵
在主導產業發展方面,江蘇走過了一條與浙江完全不同的大規模制度變遷之路。與浙江市場自由選擇模式相比,江蘇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方政府推動的。與浙江以民營企業自發為主模式不同,江蘇模式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由於江蘇的地方政府處於強勢地位,有效地推動了江蘇的經濟發展。另外,在發展民營經濟的政策需求和政策供給方面,江蘇與浙江有著本質的差別。主要體現在:
首先,雖然政治約束在兩地的制度轉型過程中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以溫州模式為代表的浙江民營經濟,在過去的20多年發展歷程中,始終在風雨坎坷的政治變化中堅持發展、不斷壯大。即使在政治約束最嚴厲的1989-1991年間,中央先后3次派調查組到溫州調查私營經濟問題,地方政府都能頂著壓力,組織有關方面有策略的向中央調查組匯報情況,使得調查組最終得出對溫州經濟發展的肯定意見。在浙江私營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1979-1982)和快速發展階段(1983-1992)大約13年中,江蘇基本上處於“沒有大動靜”狀態,對發展民營經濟的制度創新和政策改進,沒有多少實質性的貢獻。
其次,在大規模民營經濟發展的制度變遷路徑上,浙江的私營經濟是一種自下而上的民本經濟,即由老百姓而非政府創造的民有、民營、民享的老百姓經濟,地方政府充當了降低大規模制度變遷的“摩擦成本”的角色。浙江民營經濟模式的制度創新,始終具有原生和先發性。江蘇模式制度變遷路徑的特點是,它客觀地選擇了一條注意規避政治風險、充分利用選擇機會集合和模仿學習效應,並力求在模仿學習中延伸、擴展和創新先行者經驗的制度變遷之路。
再次,與浙江民營經濟模式具有原生性的特點相比較,江蘇民營經濟模式主要是在原有體制中強行成長起來的“次生型”形態,這種大規模的強制性制度變遷,使得江蘇模式更多的帶有非市場經濟的痕跡,政府主導性因素比較明顯。受此約束,身為近代工業的搖籃的蘇南地區,對上海的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業產生了先天性的依賴,制造業高度發達,但服務業相對較弱。
最后,兩種模式雖然在發展的路徑、時間、方法等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別,但存在殊途同歸的發展前景。江蘇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導力量一直很強,浙江自下而上的政策創新和創業能力較強,企業家精神也很強勁。不過,江蘇人擅長模仿創新和經驗總結,由於制度創新和政策創新作為“公共產品”的近似於免費的充分利用,使得兩種模式的民營經濟發展模式的殊途同歸趨勢正在加速。
軟硬件基礎設施配套是模式成功保障
改革開放以來,工業化和經濟增長是長三角城市群形成和發展的主要原因。在江蘇和浙江發展的早期階段,經濟增長是城市群形成和發展的原因﹔而在后期階段,城市群發展是經濟增長的原因。
有所不同的是,浙江民營資本經濟推動的私營經濟發展模式,在發展過程中日益顯露出需要地方政府發揮引導公共基礎設施投資、組織規模經濟和抵御市場風險等功能,以提高區域經濟活動的社會效率﹔而江蘇以地方政府推動的私營經濟發展模式,也急需在市場化轉型過程中轉變政府職能的方向,減少政府干預,重點培育自下而上的區域創新能力。兩者的創新方向是趨同的,在市場機制的基礎上、由政府引導民本經濟。通過各種軟硬件基礎設施的優先增長,來統籌協調並引導產業空間均衡布局,是兩種模式成功的重要保障。
(作者為南京大學商學院教授、南京大學長三角研究中心研究員。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支撐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新戰略區域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4ZDA024)
(來源:《中國經濟報告》第8期)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