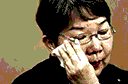人民網北京9月22日電 (呂騫)中國的農村土地改革歷來有實踐先行的傳統,但政策何時能趕上實踐的步伐,與現存法律沖突之處應如何化解,仍存在爭議。
中國農業大學與相關機構專家共同發起組建的“中國土地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揭牌儀式上,來自國務院法制辦、國土資源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機構的專家與領導,圍繞農村土地改革進行了激烈的探討。
實踐先行 農村土改到了不推進不行的地步
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介紹,從去年調研北京、廣東佛山等地郊區的情況來看,盡管農村集體土地的轉讓、抵押、租賃等政策還未出台,但相當大部分的村庄已經在做了,實踐早走在了政策的前面。
“就類似孩子已經生下來都要上學了,但是還沒有戶口”, 劉世錦感嘆,農村集體土地制度改革已經到了不推進不行的地步。
用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宋洪遠的話來說,就是“群眾都已經過河了,干部還在摸石頭”。
對此,國土資源部副部長胡存智坦承,現有土地制度存在很多不適應、不可持續、需要進一步改革的方方面面,改革的呼聲很高,但如何找到適合中國的土地改革路徑,仍需要加強研究,凝聚各方共識來共同推進。
農民不種地:土地從兩權分離走向三權分離
回顧歷史,中國的農村土地制度經歷了建國初期的農民個人私有制、50年代的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家庭聯產承包制。家庭聯產承包制將承包經營權從所有權中分離,土地的所有權歸集體,但承包經營權歸農民,兩權分離極大地解放了農村生產力。
但隨著城鎮化進程的推進,大量農民離開土地走向城市,農民雖然承包土地,但負責經營土地的往往另有他人,土地的承包權與經營權進一步分離。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局長趙陽介紹,從2014年6月全國數據來看,全國流轉耕地面積3.8億畝,佔全部承包地的28.8%。其中,出租和轉包方式(非自耕農方式)佔78.6%,完全轉讓承包權方式佔6%,再次轉讓方式佔3.2%,即是說實際上三權分離已經是一種非常普遍的狀態,經營權不在承包者手裡這種現象佔比較大,涉及大概26%左右的農戶,三權分離現象已經客觀存在。
土改的核心:如何解決經營權的擔保抵押
十八大后,中央召開的農村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關於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講話,內容是:“穩定堅持農村集體土地所有制,穩定承包經營權,放開搞活經營權”。
“經營權放開搞活的核心問題是要解決抵押、擔保的問題”,國務院法制辦副主任甘藏春表示。
目前,《農村土地承包法》、《物權法》、《擔保法》等法律更加強調農用地的社會保障功能,均對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抵押作出了禁止性規定,即農民不允許直接以土地的承包經營權進行抵押。
雖然承包經營權不允許抵押,但是農民自己若不種地,而是將土地轉包給他人進行經營,即將承包經營權中的經營權分拆出來轉讓給第三方,第三方受讓的經營權能否進行擔保抵押?這一問題在法律上並不明晰,也成為此次土改的核心。
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在落實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的基礎上,穩定農戶承包權、放活土地經營權,允許承包土地的經營權向金融機構抵押融資。
作為起草組成員之一,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局長趙陽在討論中表示,雖然現行法律規定承包地不能進行抵押,同時《擔保法》第75條規定債權、股票等可以用來質押,即經營權的收益權可進行抵押,但第74條同時又規定,質權和債權不能同時存在,質權消失的同時債權也消失。因此,難以解決抵押融資的問題。
趙陽同時也提出,承包經營權不允許抵押,但其派生出來的經營權卻允許抵押。反映到現實中即是這樣一個困境,農民不能將手中的土地承包經營權進行抵押,但其轉包給他人之后卻又允許抵押了,這似乎難言合理。
“假如農民將土地轉包給自己,是不是就可以做抵押了?”趙陽設問道。
甘藏春表示,承包經營權已明確為用益物權,那麼經營權到底是債權還是物權呢?假定只是債權,那麼抵押、擔保便在法理上說不通。抵押的到底是什麼,應該在經營權權能上進行更細致的劃分,不能簡單地套用傳統的民法和物權法理論。
“土地所有權權能的配置、分化和細致,是下一步改革的唯一出路。”甘藏春總結道。
對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副部長劉守英也表示必須通過集體所有制的深化改革,重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使用權、轉讓權權利體系,為農民提供完整的、權屬清晰的、有穩定預期的土地制度結構。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