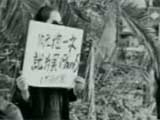近期,發生了寧波PX項目遭遇公眾大規模抵制事件,最終以市委、市政府宣布堅決不上PX項目、並停止推進鎮海煉化擴建一體化項目的前期工作而暫時告終。從近幾年相繼發生的廈門PX、大連PX、什邡鉬銅、啟東排污到最近的寧波PX事件不難發現,事件的演變基本遵循一個套路:政府悄然上馬——項目遭到民意反對——官民博弈——事態升級引發沖突——地方政府妥協——項目取消或暫緩。這些事件的發生不僅在國際社會造成了較大的負面影響,更給地方政府的決策行為帶來了嚴峻挑戰。顯然,敏感項目靠街頭裁決非長久之計,汲取上述系列事件的教訓,直面日益高漲的公眾環保意識的覺醒,改變既有的項目引入機制,既有助於避免今后類似事件再次發生,也有助於提高政府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水平。
“面朝大海”式重化工業潮的市場邏輯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經濟國際化程度不斷提高、產業鏈的深化以及加工趨於復雜化和高端化,中國經濟發展最引人注目的現象是制造業整體開始實現從輕型化制造向重型化制造的轉型,重化工業浪潮席卷中國大地。“中國制造”所獨有資源驅動與外需拉動的兩大特征,使得東部沿海地區成為了制造業優先集聚之地。其密集的港口、通達的水陸運輸線、高密度的城市和人口,是發展制造業所獨有的區域優勢,對於資源外部依賴性更大的重化工業來說,尤為顯著。
隨著“三大四小”經濟圈帶規劃(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三大經濟圈和北部灣經濟帶、海西經濟帶、江蘇沿海經濟帶、遼寧沿海經濟帶四大經濟帶)以及“三區”發展規劃(浦東新區、天津濱海、珠海橫琴)上升為國家戰略,沿海地區率先發展成為我國區域發展戰略的重中之重。在國家“7918”高速公路網、“四縱四橫”高速鐵路網和五大港口群陸續建成后,一條長約3000公裡、縱深寬約200公裡的東部沿海將成為環太平洋乃至全球的一個重要經濟帶,在未來世界經濟競爭格局中佔據重要一席。在新一輪產業轉型升級和國際產業轉移浪潮中,東部將整體“面朝大海”,依托港口發展的資本密集型、高端制造型的鋼鐵、石化、造船、航空、高鐵制造等重化工業將重點轉移到該經濟帶內。
PX(Para-Xylene,對二甲苯),作為重要化工中間品,是生產滌綸、塑料、膠片、磁帶、光盤、磁卡等眾多產品的原材料,其生產加工被譽為“黃金產業鏈”。隨著“中國制造”規模的膨脹,其需求急劇上升,巨大的市場缺口本身也意味著巨大的商機,加之石化產品資本密集、產品附加值高,是當前經濟衰退形勢下各地尋求經濟突圍的最佳選擇之一,這也是沿海各地政府對石化大項目趨之若?的內在市場邏輯。
“鄰避效應” 挑戰敏感項目引入機制
為何在鋼鐵、石化、造船、飛機、高鐵等眾多重化項目中,唯有PX等石化項目引起公眾敏感呢?首先,因為石化產品的生產過程具有較大的環境風險,一旦發生極端事故,如發生危及該項目安全的自然災害、戰爭和恐怖威脅,后果將不堪設想。其次,石化生產過程還會產生排放許多有毒的污染物,對附近居民的健康產生威脅。再次,石化產品尤其是中間體本身也不同程度具有毒性,包裝、儲藏、運輸等環節的泄露也會給周邊環境帶來影響。
因此,PX等重化工項目具有與垃圾場、核電廠、殯儀館等鄰避設施相似的“鄰避效應”(Not-In-My-Back-Yard,NIMBY Effects)。鄰避項目產生的稅收、就業、治理等積極效益為全社會所共享,但污染、噪音、輻射等負外部效應卻由附近居民來承擔,自然受到選址周邊居民的反對。環境經濟學發現,“鄰避效應”與信息披露等呈負相關,而與政府強制力等呈正相關。事實上,環境服務也是一種公共產品,並且是一種具有正常商品(Normal Goods)特征的公共產品。隨著收入增加,正常商品的需求量會上升。換句話說,當人們更
加富裕后,往往會發出“要命不要錢”的吶喊。這也是為什麼多數PX項目在發達城市受抵制,而在落后地區相對容易落戶的根本原因。南沙石化項目移址湛江東海島,廈門PX項目移址漳州古雷半島,固然有選址更加科學化的原因,但不可否認,“鄰避效應”的強弱也是決定移址能否成功的關鍵。
許多學者呼吁,應對現有我國沿海重化工業項目分散布局、重復布局的現象引起高度重視。從我國海岸線北端的渤海灣開始,一路逶迤南行,直到大西南出海口北部灣,在漫長的海岸線上,諸多地點矗立著龐大的儲油罐、高聳的反應塔和巨型的高爐。在強大的GDP驅動下,地方政府對石化項目的引入紛紛採取低價供地、稅收優惠、強力上馬等竟次博弈(Race to the Bottom)措施,導致沿海地區石化產業園區建設雷同。這種現狀與國際上對重化工普遍實行的集中布局、集中整治原則相悖,潛伏著巨大的環境隱患。尤其引起注意的是,目前,PX等石化項目採取“捏軟柿子”的被動選址方式不是長久之計。即使今天在政府強制力干預下PX等石化項目在當地落戶了,如果配套治理能力跟不上,在日后當地居民收入上升、環境意識不斷覺醒后,建成項目也會因環保沖突而被迫停產、搬遷。
以“公眾利益至上”為原則
從輕型制造向重化制造轉型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大勢所趨。當下緊迫的任務應當是採取相關措施,充分彰顯民意,改變政府角色和決策行為,強化對土地、環境等初級要素的硬約束,避免重蹈經濟外延式擴張的 覆轍和重化工業的低端化回歸,拒絕“灰色重型化”,實現 “清潔重型化”。
一是應改變目前政府在項目引入中的“投資人利益至上”局面,變“政府供地”為“市場供地”。目前影響項目利益的關鍵點在於,政府為了討好投資人,普遍採取“政府供地”的模式,把本應由投資人承擔的土地、環境等成本和風險攬到政府自己身上,其結果自然是政府坐在投資人的板凳上來裁決項目,發生漠視公眾利益的決策現象也就難以避免。因此,應變“政府供地”為“市場供地”,讓投資人與利益相關者進行談判來決定項目的落戶與利益分配,而政府隻扮演中間人的角色。
二是強化對現有石化項目的環境治理,改變公眾對石化項目的環境預期。應採取更加嚴厲的環保措施來改變目前石化項目污染大、環境責任意識薄弱、風險控制能力不足等狀況,改變目前公眾對石化項目的負面印象。許多學者和政府官員往往拿國外石化項目沒有污染或低污染來說事,試圖勸說公眾消除對石化項目的恐懼心理。筆者曾參觀過德國路德維希港的巴斯夫股份公司(BASF SE),其工廠離居民區最近處確實隻有一街之隔。然而,巴斯夫的環保治理堪稱世界一流,其城市的空氣質量遠比國內許多環保模范城市還好。但國內的化工項目遠遠達不到巴斯夫的水平。眼見為實,公眾更相信眼前的事實。因此,政府必須以事實來信服公眾。
三是提高環評的公信力,強化全過程監管。引入第三方環評是國際通行做法。但這一制度的前提是社會誠信體系發達,第三方具有獨立性。現有環評機構受政府干預太多,許多大項目環評往往是走過場,甚至一些項目是“先上車,后補票”,環評成了支持政府決策的工具。事實上,無論是環評、監管、信息披露等,公眾參與的程度遠遠不夠,公眾的利益難以表達,往往被迫採取極端的行為來抗議。
四是建立敏感項目的預警機制和利益補償機制。重化項目潛在環境風險大,應強化預警機制建設,強化信息披露,讓企業在社會和公眾強大監督壓力下採取有效措施消除隱患,降低風險。此外,應強化企業的環境責任意識,通過建立補償機制、環境責任險制度等,給予當地居民相應的風險和利益補償,以利益博弈而非“霸王硬上弓”的強力方式來引導項目的落戶與建設。
(來源:《中國經濟報告》雜志)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