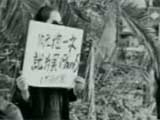有評論家指出,相比經濟增長理論,“配對理論”並不重要,可以說見仁見智,不過把博弈論的理論和方法概括為“歪門邪道”,恐怕是太過分了。整個華人經濟學界在世界主流經濟學的地位,近年來有下降的跡象,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博弈論這條腿發育得不夠強壯。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埃爾文•羅斯(Alvin Roth)與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教授羅伊德•夏普利(Lloyd Shapley)。他們的貢獻,屬於博弈論的范疇。
現代經濟學的博弈論革命
現代經濟學在20世紀經歷了兩次升華。一次是20世紀初期把微分學概念和方法引進經濟學的“邊際分析革命”,從此經濟學變得有趣,不再是“沉悶的科學”(A dismal sience)﹔另外一次是20世紀下半葉的“博弈論革命”——除了本身的成果以外,博弈論還在思想路線上改寫了整個現代經濟學,並且催生了信息經濟學,那是經濟學討論信息不對稱市場的分支。
諾貝爾經濟學獎在1994年度授予三位博弈論專家哈薩尼(John Harsanyi)、納什(John Nash, Jr.)和澤爾滕(Reinhard Selten),在2005年度又授予兩位博弈論專家奧曼(Robert Aumann)與謝林(Thomas Schelling)。此外,諾獎在1996年度、2001年度和2007年度一共授予6位與博弈論關聯緊密的信息經濟學的學者。18年來,經濟學獎6次授予博弈論的大師和與博弈論關系最密切的信息經濟學的大師,可見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在現代經濟學主流發展中的位置。
我對夏普利的經歷比較熟悉。他在哈佛大學本科學習期間,從軍來到成都地區,與中國軍民並肩抗日,並且立功受獎。二戰結束后,他返回哈佛繼續他的學業,取得數學學士學位。畢業以后,他先在美國著名的“戰略思想庫”蘭德公司工作了一年,隨后進入普林斯頓大學數學系,在塔克(A.W.Tucker)教授的指導下攻讀博士學位,塔克也是納什的博士導師。這樣,在普林斯頓大學數學系塔克教授門下,已經有兩位博士研究生后來獲得了經濟學諾貝爾獎。
早在普林斯頓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時候,夏普利已經被公認為博弈論奠基人馮•諾意曼(John von Neumann)和摩根斯滕(Oskar Morgenstern)的傳人,是合作博弈領域無可爭議的領導者,在這個領域做出了許多貢獻,包括比較容易向普通讀者介紹的夏普利值(Shapley Value)。在普林斯頓大學塔克教授主持的博弈論小組裡面,納什年紀比較小,個性也特別。參加過抗日戰爭的夏普利,因為年長一點,而且心地很好,被公認為納什的保護人。
夏普利值與權力指數
最簡單的夏普利值,是權力指數,它可以用下面的例子來說明:假定某議會一共有100個議席,議員分屬4個黨派:紅黨43席,藍黨33席,綠黨16席,白黨8席﹔假定對於一般議題的任何提案,議會實行一人一票並且多數通過的投票規則。又假設由於黨紀的約束,議員對於任何議題,都隻能按照黨的意志投票。
議會共有4個“議會黨團”,每1個議會黨團,都有可能面對其他3個議會黨團組成的各種可能的聯盟。學過一點排列組合的讀者都知道,“其他3個議會黨團”的各種聯盟組合,一共有7種:3個其他黨團抱成一團的聯盟1個,3個其他黨團兩兩抱團的聯盟3個,3個其他黨團各自成“團”的“聯盟”3個。面對3個其他議會黨團所有7種情形的聯盟,我們要看看有幾種情形可因他成為決定性的議會黨團,即他加入聯盟就能夠讓聯盟的議案通過、他不加入聯盟就可以阻止聯盟的議案通過,並且把成為決定性議會黨團情況的數目叫做這個議會黨團的“權力指數”。
現在計算他們在議會的“權力指數”。
先看紅黨,他有43席,他可能面對的7種情況,分別為藍綠白聯盟57票、藍綠聯盟49票、藍白聯盟41票、綠白聯盟24和單獨的藍黨33票、單獨的綠黨16票和單獨的白黨8票。在這7種情況下,有6種情況他成為決定性的議會黨團,於是我們說紅黨的權力指數是6。再看藍黨,他有33席,他也面對7種情況,分別為紅綠白聯盟67票、紅綠聯盟59票、紅白聯盟51票、綠白聯盟24票和單獨的紅黨43票、單獨的綠黨16票和單獨的白黨8票。在這7種情況下,他隻有面對綠白聯盟24票或者單獨的紅黨43票這2種情況,才是決定議案是否通過的議會黨團,從而藍黨的權力指數是2。運用同樣的方法,可以算出綠黨的權力指數是2,白黨的權力指數也是2。
結果出人意料:在這個議會裡面,議員數目33的藍黨,與議員數目差不多隻有他三分之一的白黨,權力指數竟然一樣,都是2。事實上,操縱一項提案是否能夠通過的“能力”,並不正比於議員黨團成員數目。四個黨的議員數目是43:33:16:8,而“權力指數”卻是6:2:2:2。夏普利值就是在分析這類問題時建立的概念和有力的工具,當然更多情形的夏普利值,會比上述權力指數復雜很多。
博弈論是華人經濟學界的短板
每次諾貝爾獎公布之前,我們這裡都有人跑出來預測一番,不過猜對的情況總是很少。這次諾獎公布以后,一位平素思維敏捷筆頭很快的財經評論家說:“最后還是忍不住吐一下槽:今年的經濟學諾獎純屬進入歪門邪道領域,我不是說博弈論的這些領域不重要,而是有很多理論比這玩意更重要。經濟學理論還是應該更加關注朴素的理論建樹,而不是奇技淫巧的一些華而不實的東西。在我看來,經濟增長理論、金融市場的穩定遠比這些所謂的配對理論要重要太多。”
這位評論家談到的那些方面是不是比“配對理論”重要,自然見仁見智,不過把博弈論的理論和方法概括為“歪門邪道”、“奇技淫巧”,恐怕是太過分了。
我倒是願意在這裡發表一點自己的觀察,就是整個華人經濟學界在世界主流經濟學的地位,近年來有下降的跡象。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博弈論這條腿發育得不夠強壯。也正是基於這個觀察,我作為一個經濟學教師,在十多年前開始,就與風車作戰,對於曾經在經濟學方面做出卓越貢獻的經濟學家貶斥博弈論幾十年發展的文字和講演,鮮明地提出商榷。令人意想不到,這樣做還是能夠取得一些積極的效果。二十年來,我也熱心地做了許多普及博弈論的工作。
“當代最后一個經濟學全才”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教授在生前就指出:“要想在現代社會做一個有文化的人,你必須對博弈論有一個大致的了解。”可是目前在我國,許多很好的大學,也隻在經濟學研究生層次開設博弈論的必修或者選修課程。
博弈按照參與人是否同時決策,分為靜態博弈和動態博弈,參與人同時決策的博弈稱為靜態博弈,參與人不是同時決策的博弈稱為動態博弈。博弈按照每個參與人是否都知道所有參與人在各種對局下的得失,分為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每個參與人都知道所有參與人在各種對局下的得失的博弈,稱為完全信息博弈,至少有一個參與人不知道其中一個參與人在一種對局下的得失的博弈,稱為不完全信息博弈。這是博弈的最基本的分類。因此,標准的博弈論課本,通常包括完全信息靜態博弈的討論,完全信息動態博弈的討論,不完全信息靜態博弈的討論,以及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的討論這樣四大部分,一個比一個難。這就是博弈論難以進入大學本科教學的主要原因。
有鑒於此,筆者與李杰博士一起寫作了《博弈論教程》,以便學生學習博弈論最容易也最基本的那些內容。這是一本難度溫和、絕大部分本科生能夠不太辛苦可以學好的博弈論入門課本。開宗明義,我們在前言中就申明,我們的材料主要集中在完全信息靜態博弈和完全信息動態博弈的范疇,並不全面。追求內容全面的教師,不宜選用我們的課本作教材。反過來說,我們相信這樣處理,雖然全面性承受了相當割舍,換回來的卻是廣大學生對博弈論的了解、熱愛和興趣。興趣和熱愛,會使往后進一步的研習變得事半功倍。我們的這本教程,恰恰寫到夏普利值為止。
我國學界的諾貝爾獎情結
有介紹文章提到,當年夏普利和納什同在普林斯頓大學,都是馮•諾意曼的學生。實際情況不是這樣,他們是塔克教授的學生。因為夏普利比羅斯年長20歲,介紹文章又說夏普利“大器晚成”。這也是想當然。筆者知道的,倒是他不隻一次成為經濟學諾貝爾獎評選委員會忍痛割愛的學者。筆者不敢對諾貝爾獎做什麼預測,只是很自然地一再提到一些大師級的學者。例如在上述2004年出版的《博弈論教程》中,筆者在前言中特別提到的,除了已經因為博弈論獲獎的哈薩尼、納什和澤爾滕以外,就隻有謝林和夏普利了。結果謝林在2005年獲獎。在《教程》第二版的前言中,沒有獲獎的博弈論大師,隻提到夏普利,——這可能和我的閱歷沒有與時俱進也有關系。結果,夏普利在今年也獲獎了。盡管如此,我仍然知道自己沒有能力預測經濟學諾貝爾獎。比如2005年與謝林同時獲獎的奧曼和今年與夏普利同時獲獎的羅斯,我就都沒有提到。
還有學者評論說:“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學者,不一定是經濟學家,甚至不一定是懂經濟學的。比如今年的夏普利。他們獲獎,是因為他們為經濟學的研究發展出了新的方法和技術,開辟了新的道路。過去納什和德布魯等獲獎,就是這樣的貢獻。”聲言過去獲獎的德布魯和納什、今年獲獎的夏普利“不一定懂經濟學”,口氣也真是太大了。
大約在兩個多月前,又有一些人在微博上議論哪些中國人可以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我完全沒有參與議論,卻冷不丁被網友點名估計什麼時候中國人會獲獎。我的回答是:“我恐怕是看不到了。但我依然樂觀地相信,在比較遠的將來,中國人可以拿到諾貝爾經濟學獎。”
我國學界的諾貝爾獎情結很重。十多年前,就有“最著名的經濟學院”院長義正詞嚴地說:“中國經濟發展得這麼好,中國經濟學家沒有道理不得諾貝爾獎”。這不知道是什麼邏輯。
經濟學諾貝爾獎的全稱,是“瑞典中央銀行紀念諾貝爾經濟學獎”(The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褒獎那些做出重大理論貢獻的學者。三十年來,國內的經濟學教育和經濟學研究,都有很大進步。這是很了不起的,因為我們幾乎是從零開始。但是必須承認,迄今在基本理論的層次上,我國學者對於現代經濟學的貢獻,基本上還是空白。可是在國人強烈的諾貝爾獎情結之下,有些朋友會一再渲染華人經濟學家誰最有可能獲獎。完全是一廂情願。
其實,如果我們能夠應用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對我國經濟改革中出現的實踐問題和政策問題提出建議,也就可以問心無愧了。至於理論原創方面,現狀是我們仍然相當可憐。偏偏在這麼可憐的背景下,我們那些最出風頭的經濟學家,走上了在“普世價值”面前堅持“中國特色”的道路。告訴學生說當年從美國學來的理論“沒有用”,轉而論証“中性政府+賢能體制+務實主義”的所謂“中國模式”,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例子。(王則柯)
(來源:《中國經濟報告》雜志)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