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培勇,著名的財稅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社科院研究生院財貿經濟系主任。兼任中國稅務學會副會長。
曾先后3次為黨和國家領導人集體學習擔任主講人。多次參與總理《政府工作報告》起草組。
代表性著作有《國債運行機制研究》《當代西方財政經濟理論》《市場化進程中的中國財政運行機制》等。
8月8日,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著名的財稅學家高培勇就稅制改革問題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
在高培勇看來,現今的稅制改革,不再只是簡單地與經濟發展挂鉤,而將是更多地與稅收制度的公共政策功能結合起來。
他認為,下一步中國稅制改革的方向是降間接稅增直接稅,具體的方法是降低流轉稅,開征財產稅和提高所得稅。其中,房產稅開征是既定政策,需要全面推開。而遺產稅與贈與稅遲早會開征。
開征財產稅,個人稅負是否會變高?高培勇解釋說,稅負的總量是既定的,不攤在財產稅上就要攤在所得稅或流轉稅上。沒有財產稅意味著中國稅制不以財產或者很少以財產作為分配稅負的標准,而這正是問題所在。有些人有很多財產,但目前不存在對個人財富征收的稅種。
從去年試點的情況來看,“營改增”實際的減稅效應大於預計效應,間接稅的減少為直接稅的擴增留下了空間,提高直接稅比重才能通過稅收調節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高培勇說,開征房產稅等不是為了增稅,而是為了進行稅收的結構性調整,讓中國的稅收制度趨向文明。
■ 對話動機
“一個國家的財政史是驚心動魄的,如果你讀它,會從中看到不僅是經濟的發展,而且是社會的結構和公平正義的程度。在今后5年,我們要下決心推進財政體制改革,讓人民的錢更好地為人民謀利益。”2008年,時任總理溫家寶在記者招待會上如此形容財稅改革的意義。
稅收和財政,就是老百姓俗稱的政府收錢和花錢的行為。改革財稅體制,“讓人民的錢更好地為人民謀利益”,關系每一個普通納稅人的切身利益。
經過30年經濟高速增長后,目前經濟發展趨緩,經濟轉型在即,而相應的財稅改革也成為經濟體制改革中重要一環。
7月23日,李克強總理表示,將持續推進財稅等“牽一發動全身的改革,為發展實體經濟和結構調整加油助力”。
十八屆三中全會在即,民眾對可能在全會上公布的若干重大改革利好充滿期待。深化財稅改革即為其一。
“新京報經濟學人”欄目選擇與普通人利益最密切的若干改革議題,尋訪這個領域最權威的學者,力圖從普通人的視角和利益為出發點,解析改革內涵,探究改革空間,尋找利益關切。
流轉稅比重高影響物價
新京報:你認為中國的稅收結構不是一種均衡的結構,而是一種畸重畸輕的結構。具體體現在什麼地方?
高培勇:從政府收入結構來看,在我國現行的預算體制格局下,並行著四類雖性質完全相同但管理規范程度差別頗大的政府預算,包括一般收支預算、基金收支預算、社會保險基金預算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
目前隻有一般收支預算是規范的,其他三類都不在規范體系之內。
按照2013年的預算數字計算,一般收支預算所佔比重僅為65%上下。其余三類收支預算所佔比重數字加總,高居35%左右。
這意味著,當前中國的政府收支規模,真正納入“全口徑”預算管理視野或完全處於“全口徑”控制之下的比重,距離當初設定的目標,還有相當長的一段路要走。這是一種失衡的情況。
新京報:單從稅收收入的結構來分析,“失衡”是個什麼樣子?
高培勇:從稅收收入結構來看,畸重畸輕的失衡狀態主要表現在兩方面。
首先表現在流轉稅和非流轉稅的比例上。以2011年為例,按照國家稅務總局口徑的統計,在全部稅收收入中,來自流轉稅的收入佔比為70%以上,而來自所得稅和其他稅種等非流轉稅的收入合計佔比不足30%。如果把流轉稅視為間接稅,非流轉稅視為直接稅,那麼間接稅和直接稅的比例為7:3。
第二個失衡的方面體現在稅收來源的結構上。2011年的統計數據顯示,來自各類企業繳納的稅收佔比為92.06%,而來自居民繳納的稅收佔比隻有7.94%。也就是說,在我國90%以上的稅收來源於企業的繳納,而個人繳納的稅收隻佔8%左右。
新京報:這種畸重畸輕的稅收收入失衡狀態對老百姓有哪些影響?
高培勇:首先,流轉稅比重高而非流轉稅比重低,導致稅收和物價的關系非常密切。這種高比例、大規模的流轉稅收入集中於商品價格渠道,向全社會轉嫁,使得稅收與物價之間處於高度關聯狀態。
而且一旦遇到通貨膨脹壓力較大、物價上漲趨勢明顯的情形,便可能推動稅收與物價交替攀升,甚至為政府控制物價水平的努力帶來不確定因素。
我國流轉稅的份額佔了消費品價格中比較大的一個部分,所以,同樣一種產品在國內和國外市場上存在價差。這種差異表面上看是價差,實際上是稅差。
假如你到紐約買件襯衫要100美元,補上稅也就是加上5%的稅,價格在105美元左右。而我國的增值稅稅率是17%,也就是含稅價格要117美元左右,這就存在差價。
提高直接稅比重才能調貧富差距
新京報:你一直強調,調節收入分配時要提高直接稅比重,為什麼?
高培勇:目前來看,隻有對個人征收的直接稅即個人所得稅才能調節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其他的稅種都調節不了。
新京報:依靠直接稅改革來調節貧富差距,需要注意什麼問題?
高培勇:現在個人所得稅已淪為“工薪所得稅”。
“工薪所得稅”放在二十年前可以有效調節收入分配差距,因為二十年前人們的收入來源比較單一,基本靠工資收入。
現在的情況完全不同,人與人之間的主要收入差距已不是工薪收入差距了,而是其他來源的收入差距。實際上,按照我國稅法,個人所得稅包括股息、紅利、財產租賃、個體經營所得等11個大項。所以居民收入分配調節必須要深入到存量。
我們至今沒有對個人財富征收的稅種。也就是說我們知道有些人很富有,有很多財產,但我們並沒有把個人財產作為征稅的依據,這是我國稅制存在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新京報:間接稅與直接稅達到怎樣的比例是合理的?
高培勇:OECD國家(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由30多個市場經濟國家組成的政府間國際經濟組織)兩種稅基本上是均衡的,間接稅大概在45%左右,直接稅大概在55%左右。我國是在往均衡的方向去調,但具體的比例不好說,比如由70%降到68%就是好事兒,並不是說非要減到50%。
需要注意的是,千萬不能說隻征直接稅,或者以直接稅為主體,我們只是說,在趨勢上是降間接稅比重,增直接稅比重。
“營改增”減稅效果超預期
新京報:降間接稅增直接稅的具體做法是?
高培勇:從減間接稅來看,目前最大的動作就是營業稅改增值稅。
從去年試點的情況來看,“營改增”實際的減稅效應大於預計效應,上海預計減120億,實際減了250億,所以“營改增”預計減稅規模的測算數字也在不斷調整。
去年中期國家稅務總局測算,“營改增”全國推廣后預計減稅1000億,而今年8月1日測算的“營改增”全國推廣后的減稅規模是1200億,這僅是指從8月1日到今年年底5個月的減稅規模,而“營改增”全國推廣后一年的減稅規模將達到3000億,這是一個不小的數字。
此外,目前“營改增”的行業范圍僅是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而不是全面的“營改增”,如果全行業推開的話,預計減稅規模將達到5000億,這是一個很大的減稅動作。另外,增值稅的現有稅率有些高,在“營改增”后續的過程中,增值稅稅率是要往下降的。
在保持宏觀稅負總量穩定的情況下,減少間接稅就為直接稅的擴增留下了空間。
開征房產稅是既定方向
新京報:在開征財產稅方面應該如何操作?
高培勇:開征財產稅一定要注意前提,前提是間接稅減少騰出開征財產稅的空間。
財產稅分三類,一是特種財產稅,二是一般財產稅,三是財產轉讓稅。目前列入方案的是特種財產稅和財產轉讓稅。一般財產稅在我國開征比較復雜,等於是一種綜合財產稅,把所有財產加起來征稅,這個目前在我國開征是比較困難的,需要假以時日。
在特種財產稅裡目前是選擇房產作為征稅對象,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房產稅。此外適當的時候要開征遺產與贈與稅,這些都在討論與研究當中。
未來假定“營改增”帶來5000億的減稅規模,那麼間接稅減下來后,這個缺口要去填補上,因為我們要保証宏觀稅負總量的穩定,在總量不變的情況下進行結構性調整,通俗地講就是個人稅負分擔結構的調整,即富人多納稅。
老百姓一般不理解,以為這種調整就是讓他多交稅,其實不是這個樣子。房產稅是肯定要征的,遺產與贈與稅遲早也要開征,做這些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讓中國的稅收制度趨向文明,讓稅收的文明程度能夠適應經濟發展水平,兩者之間相匹配。
新京報:房產稅開征遇到不少爭議,不少人擔心開征房產稅會加大自己的稅收負擔。
高培勇:開征房產稅就是一個既定的方向。但房產稅無論怎樣設計一定會有扣除和抵免。
需要說明的是:開征房產稅等不是為了增稅,而是為了進行稅收的結構性調整。
結構性調整的意思是,有人會因此多交稅,有人會因此少交稅,針對普通百姓而言就是少交稅。所得稅增加的部分主要是對富人收的。
新京報:方案的設計會以什麼作為征稅標准?
高培勇:我認為採用的標准還是會選用人均住房面積。
新京報:社科院2012年報告建議人均住房超40平米部分征房產稅。這一方案遭到六成以上網友的反對。
高培勇:是這樣的。但這也從另外一個角度反映出整個中國城鎮居民的住房水平極大提升了。
當然如果執行起來40平米可能確實有些偏少,我們可以適當增加到50平米甚至60平米,這是可以討論和設計的事情。
“我們至今沒有對個人財富征收的稅種。也就是說我們知道有些人很富有,有很多財產,但我們並沒有把個人財產作為征稅的依據,這是我國稅制存在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房產稅試點沒有遇到大的阻力
新京報:打破既得利益格局的阻力大嗎?
高培勇:非常大,因為有房階層的人數在不斷增加。特別是老百姓在找不到新的投資渠道時,就把大量的錢都投在了房產上,形成了這樣的一種利益格局﹔同時,有房人群的話語權相對比較大。
如何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其實可以有不同的思路,我們一直主張增量房征稅,就是現在上海試點的方案,開征時沒有納稅人也沒有征稅對象,如果有新的交易產生才進入征稅范圍。
新京報:存量房的利益格局不去碰?
高培勇:中國的改革是漸進式的改革,最重要的是先讓房產稅落戶中國,就像種樹一樣,先成活,然后再長大。在這個過程中,我的判斷是所有的存量房都會變成增量房,隻要一換房本那就是增量房,只是要等時間。
新京報:人們普遍認為開征房產稅的阻力很大一部分來自體制內的官員,因為他們有房產又有較強的話語權,你認為是這樣嗎?
高培勇:不能隻盯著官員,所有的人都在這個范圍之內。
新京報:從重慶、上海兩地的試點來看,阻力主要來自哪裡?
高培勇:如果從試點來看,應當說並沒有形成大的阻力。因為試點實行的都是增量房征稅。我把上海的試點方案,形容成在征稅前挖了一個大坑,對這個坑裡的人和房子征稅,開征稅的時候這個坑裡什麼都沒有,以后這個坑裡人和房子就會越來越多,但都是自願跳進去的。這樣一來就把可能形成的阻力分解或者減弱了,改革起來很平穩。
新京報:不少人把房產稅問題和房價過高的問題挂鉤。
高培勇:現在大家評判房產稅試點時,也就是說稅征得少了一點,房價回落得幅度小了一些。我們從來沒有把房產稅的開征同房價挂鉤,我們只是說稅收要趨向於文明,稅收負擔趨向公平合理。
房價不是我們要討論的問題。我們關心的是大家有房可住,房價的問題要交給市場去調節,我們重點要解決的是窮人和中低收入者的住房問題。
新京報:房產稅如何加強稅源的控制?
高培勇:這個屬於技術上的問題,我們的技術條件還是不錯的,全國聯網的程度比較高,隻要認真去做就可以做好。
新京報:全面開征房產稅在“十二五”期間能完成嗎?
高培勇:現在看很難。
稅收結構要向均衡方向調整
新京報:你多年來一直強調稅收負擔的分配要公平合理,為什麼?
高培勇:稅收負擔分配公平合理關系稅收文明問題。稅收的文明程度與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水平是相對應的。人類對稅收文明的追求就是稅收負擔的分配要公平合理。
新京報:怎麼去理解稅收文明?
高培勇:稅收文明主要體現在稅制結構上。稅制結構解決什麼問題呢?解決的是稅收負擔分配的標准問題,即按照什麼樣的標准去分配稅收負擔。
舉個例子,假定5個人組成一個小社會,這5個人要共同負擔50元的稅收費用,這50元的費用負擔應該如何分配?
第一種分配辦法是平均分配,一個人交10元,這種分配方式不夠文明,是一種近似野蠻的分配方式。人類最初的稅制就是這種,叫做“人頭稅”,不考慮個人的收入差別和受益程度。這種稅制我們稱為簡單原始的直接稅階段,這是第一種稅制階段。
第二種稅制階段為間接稅階段,比第一階段文明一些了。間接稅階段不是簡單原始的平均攤到每個人的身上,而是按照消費多少負擔稅收。比如5個人都要喝水,那就把50元的稅收負擔攤到到水的價格中,誰買水誰交稅,不買就不用交稅,多買多交稅。
我國目前就基本處於第二階段,以流轉稅為主體,也就是按消費情況負擔稅收,稅收包含在商品的價格中,隻要買東西就交稅。
第三種稅制階段有兩種分配方式。
其一是按照個人收入比例分配,比如5個人負擔50元,收入高的可能要掏20元,其他四個人按比例分擔剩余的30元。收入高的承擔的稅負多,低的承擔稅負少。
其二是按照財產比例分擔稅負,比如按照房屋的價值分擔稅負。這是發達的直接稅階段,發達的直接稅顯然更合理。
現實生活中,實行的都不是單一稅制,而是復合稅制,即稅收負擔分配標准多元化,既可能按照消費分配,也可能按照所得分配,還可能按財產分配。所以稅收有三大體系:流轉課稅、所得課稅、財產課稅。
中國目前的情況看,絕大部分是流轉課稅,按所得課稅和財產課稅的比重都很低,甚至財產課稅基本上沒有。所以,我們的稅收結構要向均衡的方向調整。
新京報:稅收文明與經濟發展程度是如何相關的?
高培勇:整個人類的經濟發展水平很低的時候,稅收分擔是比較簡單原始的﹔隨著經濟的發展,有了商品交易,才會有間接稅﹔經濟繼續發展,人們的收入達到一定的水平,財富積累到一定的階段,自然會過渡到以所得和財產課稅為主。
新京報:有觀點認為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還沒有達到直接稅和間接稅均衡的階段,對此你怎麼看?
高培勇:我不這麼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有幾個衡量指標。第一個是GDP指標,我國GDP總量目前排名世界第二﹔第二個指標是家庭財富總量,即中國人的財產總和,這個指標在未來兩三年內也會達到世界第二。
同時,追溯人類稅制結構的演進歷程會發現,在很多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還沒有達到我國現階段的經濟發展水平時,其稅收文明程度就已經比我們現階段要高了。以個人財產稅為例,目前國際上基本隻有中國這樣的國家不征財產稅。
新京報: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
高培勇:這與我國的社會制度是有關系的。以前,老百姓基本上沒有財產,房改以后才有了房子,再加上近十幾年經濟的突飛猛進,人們的個人財富才越積越多。
新京報:一些老百姓會覺得,擴大直接稅,個人稅負就變高了。
高培勇:這是誤解。千萬不要理解成:有財產稅稅負就高,沒有財產稅稅負就低。因為稅負的總量是既定的,政府一年要花10萬億,稅負就是10萬億的量。這些錢是要攤的,不攤在財產稅上就要攤在所得稅上,不攤在所得稅上就要攤在流轉稅上。沒有財產稅意味著我們不以財產或者很少以財產作為分配稅負的標准。
增加稅負透明:中國可考慮價稅分列
新京報:減間接稅的同時也在減企業稅,增直接稅也是在增居民稅?
高培勇:是的,我們說的就是兩個方向,減間接稅增直接稅,減企業稅增居民稅。這兩方面是一致的。企業稅包含增值稅,營業稅和所得稅等,減增值稅等間接稅實際上就是在減輕企業的稅負。
新京報:增直接稅老百姓的感受還是比較明顯的,但減間接稅的感受卻沒有那麼直觀,這個問題如何處理?
高培勇:一個是直接稅,一個是間接稅。但直接稅感受更明顯,而且大家擔心間接稅沒降下來直接稅又升上去了,這是問題。
未來我們主張進行一項改革,就是間接稅透明化,稅價分列,比如手機5000元,實際上成本加利潤3000,含稅1000多元,在銷售的時候,稅價分列,分別標明哪部分是實際價格,哪部分是稅,這是使中國的稅收透明的一種方式。
新京報:減間接稅的過程中物價會降下來嗎?
高培勇:在減稅的過程中物價應該是會下降的。
新京報:從目前的社會環境來看,老百姓一聽到增稅,反對聲音是非常大的,稅改是否會因此受到很大的阻力?
高培勇:會的。盡管經過了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普通百姓對稅的了解程度仍然是很低的。大家好像都懂稅,但實際上又不懂稅,甚至包括官員和社會上層人物也不怎麼懂稅,這和我們中國的歷史有關系。
建國以后很長時間,我們在宣傳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時說,社會主義國家的老百姓個人不交稅,稅是由企業來交的。所以經過長時間的熏陶,老百姓覺得稅收是和自己無關的,現在突然增加稅,感覺有些受不了。
另外,由於長期覺得稅收與自己無關,大家也不清楚整個稅制架構是怎樣的。比如我們說,在稅負總量鎖定的情況下,稅制結構的調整實際上是不同人群承擔的稅負發生變化,但很多人都不知道這些,只是覺得向我征稅了,我就要多交稅了。殊不知其實是“背著抱著一邊沉”,直接把稅負攤到個人身上,還是通過售賣物品時加價給你,其實都是從你兜裡掏錢。
比如2011年山東濟南的一名政協委員在提案提到,饅頭稅的稅率高達17%,結果引發對饅頭稅的爭議,實際上這樣說來,何止有饅頭稅,還有礦泉水稅,隻要是消費品都有稅。所以讓老百姓懂稅是需要一個過程的。
“如何打破既得利益格局?其實可以有不同的思路,我們一直主張增量房征稅,就是現在上海試點的方案,開征時沒有納稅人也沒有征稅對象,如果有新的交易產生才進入征稅范圍。”
記者 李蕾 楊萬國 實習生 安百隆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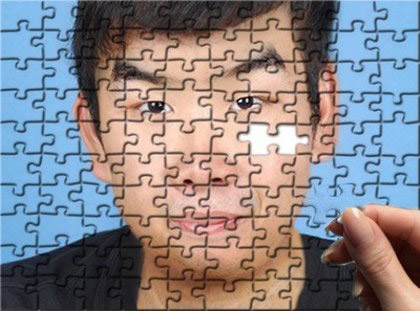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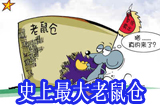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