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資藥企在華行賄風波愈演愈烈。繼葛蘭素史克(GSK)因涉嫌在華行賄被立案調查后,英國制藥巨頭阿斯利康23日也被中國警方展開調查,其他一些跨國藥企輝瑞、羅氏、優時比也先后傳出類似丑聞。不過,在西方媒體筆下,這些跨國巨頭在中國“栽”得冤枉,它們是“在中國出污泥而被染”,該怪罪的似乎應該是“被腐敗吞噬的中國醫療系統”。但其實,與能挽救人類生命的醫藥本身不一樣,無論是在腐敗情況相對嚴重的發展中國家,還是在監管更嚴格的美歐,一本萬利的西方醫藥行業一直受到賄賂等丑聞困擾,德國洪堡大學國際問題專家霍爾特曼24日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美歐跨國醫藥巨頭頻發的賄賂丑聞絕不僅僅是“環境綜合征”,更是自己的基因和文化的失敗:在巨額的利潤面前,尋歡作樂和賄賂已經無關道德問題,而被視為正常。他說,在高貴的醫學淪為賣狗皮膏藥行業之前,各國應聯手重新審視醫藥行業的潛規則,無論是在世界哪個國家。
跨國藥企,真的“從錯誤中學到了”嗎?
“葛蘭素史克事件發生后,跨國藥企幾乎整體自危,公司總部也第一時間派人進行嚴格的自查。”像某跨國藥企經理這樣對自己公司陷入反賄賂調查的擔憂這兩天並不少見。繼上周比利時藥企優時比証實已接受了中國國家工商總局的調查后,英國制藥巨頭阿斯利康23日又有兩名上海員工被警方傳訊。美國彭博通訊社稱,默克、諾華、羅氏等全球知名藥企也涉嫌於最近3年內通過同一家旅行社進行過會議和行程安排。這家旅行社被認定為替葛蘭素史克將部分會議費用套現,來行賄以打通關節。
不少西方媒體都把這歸罪於是中國環境使然。不少美歐媒體宣稱,跨國藥企只是“入鄉隨俗”,它們難以抵擋中國社會貪腐賄賂的社會風氣。英國《獨立報》說,葛蘭素史克在中國是“出污泥而被染”。路透社在報道中更隻字不提西方藥企的責任,卻指稱葛蘭素史克“行賄門”背后暴露出的是中國醫藥市場的“混亂和丑陋”。在中國的醫療體系中,“賄賂已經是必需品,成為幫助中國公立醫院維持運作的潤滑劑。如果中國醫生沒有非法酬勞的話,健康系統很難發揮正常作用”。
這種“環境論”和“入鄉隨俗說”也成為一些跨國公司在國外搞腐敗的托詞。中國警方查辦此案后,葛蘭素史克公司總部發表一份聲明,將責任推到“某些員工及第三方”身上,聲明稱,“對本公司某些員工及第三方機構因欺詐和不道德行為所面臨的嚴重指控,深表關切與失望。上述行為嚴重違背了葛蘭素史克全球的規章制度、管理流程、價值觀和標准。葛蘭素史克對此類行為絕不姑息和容忍。”但有業內專家質疑,問題在於,該公司在全球的制度、價值觀和標准以及管理流程既然如此嚴格,為何其在中國分公司的高管能夠“逃避公司流程和監管進行不當操作”?
實際上,葛蘭素史克去年就曾為賄賂丑聞付出過高昂代價。英國廣播公司稱,2012年,葛蘭素史克公司同意支付30億美元巨額款項,就欺詐等罪名與美國藥監當局達成史上金額最大的和解案。美國司法部當時稱,葛蘭素史克對三項刑事指控認罪,並涉嫌在美國以赴夏威夷豪華游及百萬美元酬勞的巡回學術演講等方式賄賂醫生開該公司產品的處方。該公司CEO安德魯·維蒂事后曾表示,“我們已經從錯誤中學到了”。
英國《衛報》稱,看來維蒂所保証“學到的經驗教訓”是沒有意義的。文章稱,我們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事實:醫藥業只是一個和其他生意類似的產業,不比其他公司更高尚。它們會盡一切可能達到目的,不論是否意味著要更改科學報告,行賄學者和醫生,或未經授權而推進“灰色”市場。畢竟,包括阿斯利康、禮來、輝瑞、默克等幾乎所有跨國醫藥巨頭都接受過賄賂調查。
環境使然還是基因作怪?
德國洪堡大學學者霍爾特曼對《環球時報》記者稱,各種研究顯示,醫藥行業已經成為最黑暗的行業之一,因為這些藥企實在是“一本萬利”。對老百姓來說,他們無論是對藥物還是這個行業完全不懂,而又離不開醫藥。霍爾特曼認為,美歐醫藥巨頭在各國賄賂案頻發有環境原因,但很多跨國巨頭本身存在著這方面的基因和文化。包括中國在內,不少發展中國家的法制的確有許多漏洞,社會腐敗現象蔓延,也是不爭的事實,但那些跨國藥企也並非無辜羔羊:利用各國市場的差異和漏洞作奸犯科,以達到牟取暴利的目的,本就是許多跨國藥企的一貫做法。
去年,全球制藥業“老大”輝瑞公司也曾陷入“行賄門”的麻煩之中。美國証券交易委員會(SEC)指控其在意大利、保加利亞、捷克、哈薩克斯坦、俄羅斯等8國的子公司和代理對當地官員和醫生行賄。據稱,輝瑞在這些國家的子公司和代理對當地官員和醫生行賄數額達200萬美元以上。為掩蓋行賄行徑,輝瑞將這些費用列為促銷、營銷、培訓、差旅、臨床測試、貨運、會議和廣告等合法支出。美國証交會打擊海外行賄行動部門負責人卡拉·布洛克邁耶當時曾感慨稱,這些制藥公司“在一些國家的分支機構將賄賂行為與其銷售文化纏繞在一起,向那些他們認為是優質客戶的海外官員推行‘積分獎勵’計劃,以此提供不合法的回報。”
法國《世界報》稱,一些跨國藥企在海外普遍實施賄賂方式多種多樣,包括提供時髦數碼產品、旅游獎勵等,還美其名曰為“業務拓展”,並通過虛立發票名目加以掩飾。為了在某些審批較嚴的國家打開市場,他們更直接對政府相關主管部門官員進行“銀彈攻勢”。腐敗情況較為普遍的非洲和拉美成為這種“攻勢”的重災區。1998年,強生公司就被美國司法部和SEC指控涉嫌在希臘、波蘭、羅馬尼亞等國進行賄賂。禮來公司也並非僅在中國一地作奸犯科,去年12月20日,SEC指控該公司涉嫌在巴西、俄羅斯、波蘭等國向政府官員或相關機構行賄,時間跨度長達15年(1994年-2009年).
即便法律體系完善、監督機制嚴密,看似無隙可乘的發達國家,某些跨國藥企也不放過任何可鑽的孔子。美國司法部2008年的數據顯示,2003-2007年間,僅西門子醫療集團一家,就涉嫌向美國5家醫院行賄,成功換取價值2.95億美元的醫療設備訂單,為此支付賄賂款達1440萬美元。在英國,強生公司也曾因類似行為被英國重大詐騙案監察局調查。德國《明鏡周刊》日前稱,德國僅2012年一年就有近1000起針對醫生行賄的案件,其中480起涉及德國醫藥巨頭Ratiopharm向醫生行賄。
更嚴重的賄賂不僅發生在藥品銷售方面,更發生在藥品臨床試驗環節上。由於美國藥監部門在審批藥品上市申請時,80%情況下需要至少一項外國臨床試驗,某些跨國藥企就通過賄賂海外主管官員和醫生,在臨床試驗環節弄虛作假,隱瞞事故發生率和藥品副作用風險,騙取上市機會,而不惜給病人和社會帶來潛在隱患。德國勃林格殷格翰公司研制的抗艾滋病藥物就曾以這種手段在烏干達進行違規人體試藥,而輝瑞公司於1996年在尼日利亞進行抗生素藥物違規試藥,引發長達17年的跨國法律糾紛,尼日利亞官方曾要求索賠高達20.75億美元。 2010年12月,“維基解密”曾披露,輝瑞公司甚至為威脅尼日利亞政府撤訴,竟雇私家偵探搜集尼司法部長的腐敗証據,以此要挾后者放棄起訴。據稱,尼官方索賠金額后來大幅度“縮水”, 僅以7500萬美元了結官方追訴,就和這起“秘密行動”有關。
耐人尋味的是,不論輝瑞、強生還是禮來,面對賄賂指控,向來採取“罰款可以交,罪名絕不認”的策略,一方面在交錢換取法律和解方面慷慨大方,另一方面,對各種腐敗和不正當商業行為指控,通常採取“既不承認也不否認”的辦法加以應對。
葛蘭素史克在這次的聲明中並未使用“行賄”一詞描述自己的行為,將“賄賂丑聞”稱為“欺詐和不道德行為”, 輝瑞在去年聲明中也全部代仰臥以“令人失望的不當支付事宜”。這主要是因為一旦認實指控,就等於落下案底,會從根本上損害這些跨國藥企及其產品的市場聲譽。
在中國無需賄賂也可成功
“醫藥領域的商業賄賂一直是這個行業的頑疾,各國政府都在打擊,但在利潤和業績壓力驅動下,給醫生‘銷售提成’的營銷模式始終揮之不去。”一名醫藥行業專家這樣稱。國際上對跨國藥企這種營銷模式也開始反思。哈佛大學教授瑪利婭·安吉爾在《制藥業真相》一書中披露,消費者因這種“灰色”的銷售推廣而承受了至少30%的漲價,這些推廣活動是必需的嗎?實際上,跨國藥企這種僅盯著盈利的價值觀和營銷模式如果不改變,賄賂丑聞很難遠離它們,藥品價格也難以根本下降。有分析稱,像葛蘭素史克等跨國藥企在各國的賄賂門常以罰款和解告終,這很難對制藥巨頭的賄賂沖動產生根本遏制。
總部位於德國柏林的“透明國際”組織東亞區及新擴展區高級主任廖燃24日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葛蘭素史克在華賄賂中國官員和醫生只是跨國藥企不規范行為的“冰山一角”。中國正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中,會出現一些政策漏洞,一些國外企業就通過中國官員“鑽空子”。
廖燃稱,醫藥腐敗並不是中國的“獨家問題”。不僅金磚國家有這樣的問題,中東歐國家在這個領域也有嚴重問題,西方國家也屢屢爆出問題。他認為,中國應該按照聯合國相關公約修訂刑法,加強對賄賂的定罪和執法,同時進行國際合作,加強對跨國公司的威懾力,有力打擊賄賂。目前,英國和美國已經在打擊海外腐敗方面走到前列。如英國公司在第三國賄賂,英國就可以起訴自己國家的公司和第三國的公司,並進行執法。
英國《金融時報》稱,對於中國的腐敗問題,觀感不一定等同於現實。隻要遵守正確的程序,海外公司也可以在中國取得成功,而無需求助於賄賂。跨國公司在中國的確面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考慮到中國市場的龐大規模及在華開展經營活動的海外公司的數量,葛蘭素史克行賄案等被媒體密集曝光的案件隻聚焦於極少數公司。隻要保持應有審慎,增強對文化復雜性的理解,建立適當的促進守法的項目、技術和工具,並對員工進行全面培訓,跨國公司可以非常成功,無需冒腐敗的風險。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人人 分享到QQ空間
分享到QQ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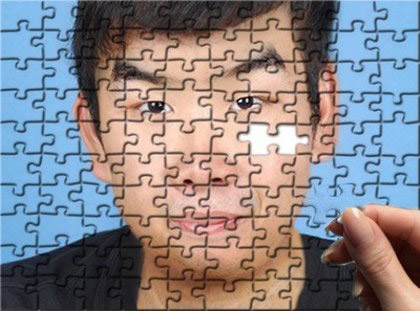








 恭喜你,發表成功!
恭喜你,發表成功!

 !
!





















